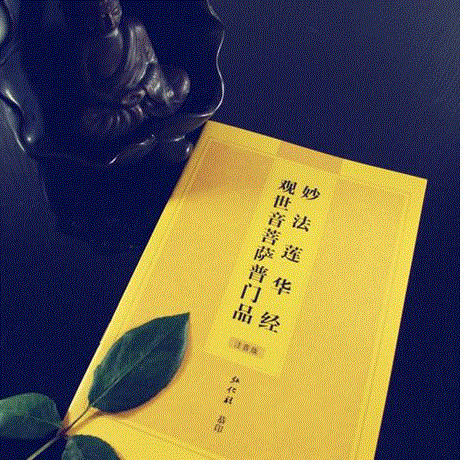张文良教授:庭前拍子翠色闲
发布时间:2024-12-03 03:04:23作者:普门品全文网青山何处不道场
从谂禅师少小离家,先在南泉处得悟,后云游天涯,到处参访。晚年尝云,“老僧行脚时,除二时斋粥是杂用心处,余外更无别用心处也。”其精勤修道之精神可见一斑。唐会昌年间(841-846),武宗行“沙汰”之制,劫波浪起,*轮摧折。谂禅师亦隐匿于家乡徂徕山(今山东泰安市东南)。其间岩栖涧汲,草衣木食,艰苦至极。然生活愈艰,仪法愈峻,未尝一日暂弛。其操守之坚,气节之贞,不让古德。待风平浪息,禅师不顾年迈,重又踏上行脚之途,据说禅师要到五台山瞻礼文殊菩萨,一位大德作偈留云:
何处青山不道场,何须杖策礼清凉?
云中纵有金毛现,正眼观时非吉祥。
禅师问:“如何是正眼?”大德无对。这位大德“何处青山不道场”,气象颇大,其后两句,指明佛、菩萨不可以相求,表现出对禅一定程度的体悟和理解。但他对“正眼”的偏执,则又说明他还有分别心,还没有达到圆融无碍、触处皆真的如如境界。故禅师一语反诘,大德顿时无对。由于禅师德行、禅行遐迩闻名,故所到之处,信众翕然辐集。禅师说法,常无人再提出论辩质疑,这在棒喝交织、论辩滔滔的禅林,实属少见。这一方面说明禅师辩才无碍,机变无方,有一言九鼎之道力;另一方面也可见出禅林对禅师的推重与服膺。
唐大中十一年(857),从谂禅师受请住持赵州观音院,从此以“赵州禅师”之名驰誉天下。
禅师这时选择赵州观音院卓锡当不属偶然。禅师长年云游在外,年事渐高,禅林在钦敬之余,莫不对禅师表示关切。还在南方之时,云居道膺劝他:“老老大大,何不觅个住处?”到茱萸和尚处,为此还受了一番善意的揶揄。茱萸:“老老大大,何不觅个住处?”谂问:“什么处住得?”茱萸:“老老大大,住处也不识。”其实禅师不在南方落脚自有其隐衷。禅师得法于南泉,属慧能下之四传,他与百丈、黄檗、临济、沩仰等宗师,虽同出一源,属南禅一系,然授受有别,门庭施设有所不同。从后来禅师接引众生的方式看,比之其他禅师动辄动棒、行喝,禅师的风格要绵和、平易得多。从义理上看,南禅以明心见性为宗旨,但此“心”、此“性”皆是体、相、用的统一。真正的见性,应是即体显用,随缘现相,在日常行事中体现出宏大的气象、洒脱的风骨。所以禅师只教参禅者“吃茶去”、“吃粥去”、“洗钵去”。说到底参禅悟道都是为了得个受用,若自称见性,死守静居,不知其用,犹如贫子发财,困守钱堆,终为贫子一样愚不可及。禅师基于自己对禅的体悟和理解,形成了独特的禅风,另辟道场,举扬一家宗风,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赵州,燕南重地,冀北名区,汉代已置县,名平棘。旧志载,“燕赵之俗崇尚浮屠,庵观寺院,星列棋布。虽穷乡下邑,香火不绝。”是知佛教很早就盛行于此。观音院位于古城东南,肇建于东汉末年,隋唐以前的传承,史籍无考,延至唐代,影响始着。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前,曾于此从道深法师习《成实论》;唐代着名书法家虞世南曾在此留下“攀龙鳞,附凤翼”的墨迹。可见,当时的观音院亦是人文荟萃之法缘福地。谂禅师遍历天下而独止住于此,盖非出于偶然。
西使东来意何在
这时的赵州禅师已寿满八十,然精神爽逸,毫无耄及之态。其禅行、其道力,经由几十年的砥砺磨炼,早已炉火纯青,臻入化境。扬眉瞬目,无不有道,一机一境,莫不有禅。其接引众生,更是挥洒自如,全无滞碍。尝示众云:“老僧此间即以本分事接人,若教老僧随伊根机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即不谈玄理,不指理路,直让人于寻常日用处着力。有学人问:“未审和尚还修行也无?”师云:“着衣吃饭。”
然慕名而至者大都满怀疑虑和困惑,期望大禅师能给与明确的开示,最好是一言之下,顿然开悟。所以有的一见禅师,开口便问:“如何是佛法大意?”有的问:“如何是禅?”但问得最多的是“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是禅林非常流行的公案,其字面含义即“达摩祖师从西方来东土究竟何意?”达摩即菩提达摩,据称是南印度人。约在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由海路来中国,后于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后遇慧可,传“无门之法门”,为中国禅宗之肇始。据其弟子县琳所述,其禅法以“壁观”法门为中心,“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禅的实际境地即“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
从“西来意”的表层意蕴看,达摩西来确有其特定的含意,此即感于东土多大乘根器,特来传播自己的一套禅法及法门。如果仅限于此,这一问题不难回答。但这样的答案是不能得学人首肯的,因为以上故事是禅林内外皆知的事实。
问:“二祖断臂,当为何事?”
……
这才是以上问题的核心所在!二祖即慧可,原名光,少时博综百家,后归宗佛教,遍习大小乘义理,并曾在香山静坐修定八年。闻达摩在少林寺修道,即前往参访,但达摩很长时间都不理睬他,也未与一句教导。慧可为表达自己求法的心愿之坚切,自断左臂,置于祖师前。达摩大为感动,收其为弟子。达摩传法慧可的情景史籍是这样记载的:
(慧可)乃曰:“诸佛心印,可得闻乎?”祖曰:“诸佛法印,非从人得。”可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祖曰:“将心来与汝安。”可良久曰:“觅心了不可得。”祖曰:“我与汝安心竟。”
学人见赵州,与慧可礼达摩相似,都是发现自己的心纷扰不安,恳请禅师予以安顿。问祖师西来意,问二祖断臂之事,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敲山震虎,搅水驱鱼,欲得禅师的点拨与明示。且看赵州禅师如何回答: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下禅床。学人云:“莫便是否?”师云:“老僧未有语在。”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东壁上挂葫芦多少时也。”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如你不唤作祖师,意犹未在。”
问:“三乘十二分教即不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如你不唤作祖师,意犹未在。”云:“未审此意如何?”师云:“我亦不知。”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云:
“什么处得这消息来。”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云:
“板齿生毛。”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床脚是。”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什么处得这消息来。”
问:“二祖断臂,当为何事?”师云:“粉身碎骨。”
问云:“如何是禅?”师云:“今日天阴不答话。”
那么,赵州禅师对这一问题到底做没做回答呢?下禅床无语、天阴不答话,是回绝;答以壁上挂葫芦、水牯牛生儿、板齿生毛、床脚,是回避。因为学人所问是抽象的义理,而禅师所答则是不相干的具体事物,其间没有任何逻辑联系,通常人不会从中得到任何相关的信息,相反只会更加迷惑!所以可以说禅师没有回答,准确地说,没有对题的回答。
不做回答,首先在于这一问题本身经不起推敲,问题本身有问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有一预设命题或隐含命题,即祖师西来有意。对以上问题,无论做何种指示性回答,都首先肯定了这一预设命题。但实际上这一命题不能成立。
这里所问的“西来意”实际上是指达摩所传心法。达摩所传或二祖所承之心法是什么呢?只是无心可传,无法可承!世尊于菩提树下,无师自悟;二祖断臂,亦无所得。心法根本是传授不得,唯自证自悟到无迷悟处,直下心空便了。有人问仰山:“了心之旨,可得闻乎?”山云:“若欲了心,无心可了;无了之心,是名真了。”达摩西来,本无造作,来只须来,去便随去。怎奈一人传虚,万人传实,后人执心为有,妄生许多葛蔓。正因为祖师西来无意,故此问正如“方的圆什么样?”一样,犯了内定结论的错误,对其回答,只须否定其预设命题,从根本上断其思路。有人问大梅禅师“如何是西来意?”师曰:“西来无意!”赵州的诸种回答,也包含了同样的意蕴。

所谓佛祖以心传心,只是虚说,实则一切不可得。但心不可得,只是说此心不可以寻常理路觅得;此法不可授,只是说法不能象知识那样在师生间授受。并不是说此心不存在,或根本就没有这种心。“心空”或“无心”,是就其不同于人的肉团心,也不同于人的灵知之心,而是无形无相的存在而言的。空不碍其有,这一“本心”,就其随缘现为万相而言,称为法相;就其为成佛的根据而言,称为佛性;就其显现于人身而言称为法身,或“本来面目”,或“父母未生之前的状态”。它是万物的本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主体与客体、可能性与现实性、有限性与无限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等等区分都不存在,是融通一切二元对立的无分别状态。它不是一种实体,不具有任何具体的规定性,即它不是“什么”,而就是“是”本身;不是“存在者”,而是非“者”化的“存在”。
面对这一无分别之“本心”,人的分别心,即人的灵知之心、人的思维是无能为力的。思维把握客体,是通过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思维的手段,达到对客体本质的把握。但当这种思维去把握“本心”这一特殊对象时,其局限性马上就显露出来。因为“本心”是万法之共相,思维本身即灵知之心亦是此心之特殊形态,正象尺子不能去测量量度本身一样,思维亦无从把握作为其本根的“本心”。再者“本心”不是实体,而是一种主客未分的如如状态,以分析性为特征,以抽象为手段的思维,对“本心”的把握,充其量是一“定格”,是无限绵延的中断,是宇宙大流的截面。充满无限生机的动态的“本心”,在思维中只能呈现为固态的、僵硬的结构。这种反映已不仅是失真的问题,而是质的变换。人的思维可以去感知“它”,但感知到的已非原本的“它”。
思维不能把握“本心”,原因在于其异质性,即“本心”是活生生的、灵动的,而思维则是构架性的、静态的。但与语言比较起来,思维仍保持其主体性,仍有一定能动性和灵活性,而作为思维物质外壳的语言则更为形式化,更少灵性。如果说思维还是多层次的,多维度的,还可以对“所指”进行主体把握的话,那么语言则是平面展开的,是一维的(在文字语言中表现为二维);如果说思维之于“所指”是一种定格,语言之于思维则是一种“投影”,即多维的思维投影于一维的语言流中。
思维与语言间的维度转换非同小可,它使在思维中不同层次的概念或思想在语言中叠加在一起,正象一个立体结构投影到平面上,各部分会纽结在一起一样。这在语言中表现为大量的歧义和悖论。就“西来意”而言,看似很平常一句话,但其中潜隐的信息量很大。西来之“意”是在不同层次上被使用的,它既可指达摩本人西来之用意或用心,又可指达摩向后人传授之“心意”。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说达摩西来有意,一定意义上又无意;在一定意义上此意可说,一定意义上又不可说。但这些在思维领域可以加以区分的内涵,表现在语言中都是一句“西来意”。要回答这一问题,先得把问题本身厘清,而从这里又会引出许许多多新的问题,由此追下去,不仅不会接近目标,反会离目标愈来愈远。此即言不及意、意不达物,只是这里的物不是实体,而是“本心”。
由于思维与“所思”的异质性,由于思维、语言的局限性,人不能通过寻常理路即概念性思维去趋近“本心”,所谓拟议即差,动念即乖,才涉言路,便失真常。赵州深悟此旨,所以以种种不对题的回答,直下截断问者的言路、思路,明示其“此路不通”!从积极的方面说,即解除日常语言、思维模式对修行者的精神束缚,使其精神具有最大的自主性。
庭前柏子翠色闲
这一思维不可把握之“本心”是万法的本根。其本源性意义对世间万物都是开放的,但只在人身上达到了高度的自觉。自觉到万物的本源性意义,就能于一草一木、一机一境中,发现“本心”的存在,发现生命的真常。
时有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庭前柏树子。”学云:“和尚莫将境示人。”师云:“我不将境示人。”云:“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庭前柏树子!”
这里的“柏树子”不妨说与前面的“床脚”、“板齿”具有同样的意义,即作为否定性标识,意在荡相遣执,让人不要有所攀附,不要向外执取。这一层含义在第一番问答中已表达出来了,而且问者认识到不能于境上生执着,说明他已会得此意。但学人再问,赵州仍答以“柏树子”,其间就别有意趣了。可以说,前一“柏树子”是在方法论意义上被使用的,意在让人斩断言路、思路之葛藤枝蔓,由此回头,返求自己的“本心”,后一“柏树子”是在境界论上被使用的,它标示一种境界,真正识得本心,并没有玄奥处,不过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看庭前柏树子依然是庭前柏树子!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是内外打成一片的境界;是没有物我、主客、彼此等二元对立的境界;是没有执着、没有烦恼、平等一如、湛然真纯的境界。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但不是一个虚幻的境界。准此而着力,久之,即能完成心识的转变,即能获得一种新的观察世界的视角,拥有一种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胸襟,一种“纳须弥于芥子,掷大千于方外”的气象,一种“众生有苦即我苦,众生不尽我去度”的情怀,一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感悟,一种生死之门,任我出入的精神。禅意如水,流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禅意如诗,显现在花木虫鱼、和风细雨中。“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于此会得,可得个中三昧。
“大道只在目前,要且难睹”。“柏树子”是一象征,其间隐含着赵州禅师许多不便直说的禅悟体验和感受。但这些含义都是隐而不显的,因为说到底它并没有说明什么,在其外在形态上,它纯然是一符号。其内涵有待人们去阐释,它本身是“死”的,有待听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激“活”。在禅宗公案中,表征“本心”或与“存在”相联系的概念语句都不是知识性、概念性的,而是隐喻性的,即是“诗意”的,它不传达给人明确的知识,而是创造一种氛围,传达一种情绪、一种意向。所以其内在的意义并不是容易理解的。欲契悟禅师之心怀,不仅要有一定的禅学修养,还必须有与禅师相近的“诗意”的心怀,所以与禅师的对机,说到底不是语言的交锋,而是心灵的默契,是师生间的心心相印。就象读一首朦胧诗,需要读者的参与和再创造,听禅师的回答,也应该透过看似无意义的言句,感悟禅师的本怀,从而识得自家的宝藏,获得一种禅者的心怀。
由此可见,所谓“柏树子”只是一个“向标”,一个“指针”,指引人去探险,去揽胜。若会得此意,只管照直参去,总有海阔天空的境地;不会此意,原地打转,以至死在句下,也未可知。故于言语间讨活路,就如守株待兔、买椟还珠般愚不可及。赵州有一弟子觉铁嘴,在赵州殁后,到了崇寿法眼处,法眼问:“承闻赵州有‘庭前柏树子’话,是否?”觉铁嘴答:“无。”法眼:“往来皆谓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曰‘庭前柏树子’,上座如何得言无?”觉铁嘴答:“先师无此语,和尚莫谤先师好。”觉铁嘴不枉为赵州弟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