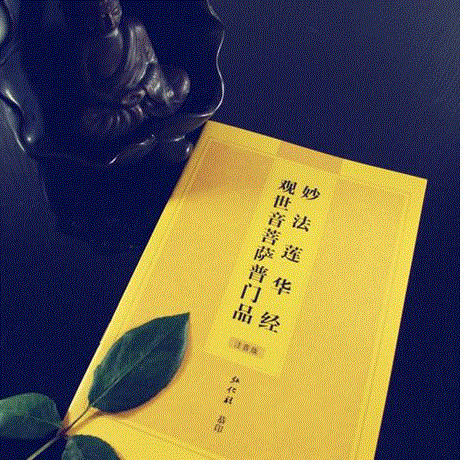宋史:宋代理学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儒佛也完成了合流
发布时间:2024-11-04 03:04:42作者:普门品全文网百家原创作者:吴昂昂谈历史
宗教可以麻醉人们的思想,有效地控制人们的行为,左右人们的欲念。宗教这一特有的属性,使统治者认识到其有利于政治,因此魏晋以来的统治者千方百计扶植、利用宗教,以便从思想上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宋代的统治者亦不例外,对宗教,尤其是对佛道采取了礼遇的政策。
宋儒喜读佛典,但并不淫佛,主要是从佛学典籍吸取养分来充实自己。但他们大多都能钻进去跳出来,由佛学经典回归到儒家正统的立场上来,这就是出入于佛、老,返求于《六经》。这一回归其价值已大不一样,他们对儒家学说的理解,已明显地打上了佛学的烙印,援佛入儒,儒佛融合实现了。
会通儒佛,是关、洛、蜀诸家共同之处。苏辙的《老子解》,就是以讲释老而又通于儒,纠合三家,其实是以老氏之学为中介,融合儒佛之说。在此书自序中,苏辙说:“僧道全与予谈道,予曰:子所谈者,予于儒书已得之矣。《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此非佛法而何?六祖所谓不思善、不思恶,则喜怒哀乐之未发也。盖中也,佛性之异名:而和者,六度万行之总名也。”
二程更是将《中庸》与禅门心法统一起来。二程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如果说宋初三先生胡瑗、石介、孙复以及欧阳修等人,对佛教的仇视不遗余力的话,那么从周敦颐、张载开始其理学思想就明显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到了二程时代,佛教对理学的影响更深,及至南宋张九成、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大师,又何尝不是援佛入儒?除这些理学家外,其他的大儒如王安石、苏氏兄弟等人,在其学说中都大量吸纳佛教内容。也可以说影响中国文化至深的宋代理学,正是北宋中叶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至此儒释互补,儒佛合流才完成了真正的历史使命。
宋儒积极“援佛入儒”,吸纳佛学精华,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新儒学,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佛教在宋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诚如清代学者陈澧所言:“自唐以后,不独儒者混于佛,佛者亦混于儒。……儒者自疑其学之粗浅而鹜于精微,佛者自知其学之偏驳而依于纯正。”这种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探究,一是佛教的世俗化,二是佛教的儒学化。
佛学传入中国,其清规戒律规定僧人不养父母不娶妻生子、不事耕稼、不蓄头发等,与中国传统礼制最根本的冲突是不拜君父,将自己凌驾于帝王之上,这与中国传统人伦纲常格格不入这一点成为儒家攻击佛教的利器。但是入宋以后,佛教与王者分庭抗礼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皇帝到寺院烧香,可以不拜佛像,这就叫“现在佛不拜过去佛”。
同时僧人也趋炎附势,升堂拈香,第一香“祝延今上皇帝圣寿无穷”;第二香“奉为知府龙图、驾部诸官,伏愿常居禄位”;第三香才轮到受业恩师。佛教的世俗化使统治者觉得它与儒学一样同样有裨于政治,因此才竭力扶持之。尽管宋代佛教待遇优厚,但在官僚体制中,仍未动摇儒家的正统地位,儒士的政治地位远远高于僧人,这一点僧人很明白,他们转向学习儒学。
智圆法师就曾明确说过:“世有滞于释氏者,自张大于己学,往往以儒为戏。岂知夫非仲尼之徒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智圆看得清楚,佛教必须依托政治才能生存,不然唐武宗灭佛的惨剧便会重演。要想生存,必须从传统儒学中汲取积极因素丰富自己,改造自己,佛教的儒学化势所必然。
佛教的儒学化必须完成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以佛为圣人与中国传统的以孔子为圣人如何解决;二是佛教的伦理与儒家的仁义礼制该厚谁薄谁。这两点解决不了,佛教的儒学化就很困难。宋初孙复、石介等人猛烈抨击佛教,其抨击佛教的关键在于以佛为圣人与儒家传统的以孔子为圣人相悖,提倡佛说即提倡夷人之伦理又悖于儒家的仁义礼乐。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儒学在改造过程中大量吸收佛教精义并形成了理学。
人们尤其是宋儒对佛教不再以仇视的态度对待之,这就为佛教的儒学化准备了前提,而贡献最大者还是佛教徒中具有相当知识水准的杰出僧侣,如契嵩等人。契嵩是一代高僧,他对宋代佛教的儒学化进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其平生著作甚丰,而得意之作是《孝论》和《原教》,这可以说是把佛教教义和佛教伦理同儒学融合的有力佐证。
在《孝论》中,契嵩以“孝道”为主题,重点探讨了佛儒伦理相通的问题,即佛之“五戒”通于儒之“五常”。在《戒孝章第七》中说:“五戒,始一曰不杀,次二曰不盗,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日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
契嵩用佛之五戒附会儒之五常,以证明佛儒是相同相通的,即“异号而一体”,因此“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亦孝乎”。“五常”是儒家的伦理原则,它与体现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三纲是儒学伦理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五戒可以附会五常,而儒学三纲则是佛教所不能逮的。但契嵩很聪明,他创造了“三本”以对应“三纲”。
契嵩在《孝论·孝本章第二》中言:“天下之有为也,莫盛于生也。吾资父母以生,故先于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于教也。吾资师以教,故先于师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于道也。吾资道以用,故先于道也。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师也者,教诰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冒也,饮食可无也,此不可忘也”在契嵩看来,既然佛之五戒能与儒之五常相通,那“道、师、父母”三本也完全可以与儒之三纲一致起来。
如果说《孝论》是契嵩把佛教之五戒三本比附于儒学之五常、三纲,使佛学向儒学转化的开端,那么《原教》更能体现契嵩在教义方面对佛教儒学化所作的努力。在《原教》中,契嵩就明言:“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欲人为善”成为儒佛共同的社会功能。不仅如此,契嵩还试图在学问上达到儒佛相通,这就是“性命”之学。
契嵩曾就《原教》的宗旨说过一段话:“夫《中庸》者,乃圣人与性命之造端也;《道德》者,是圣人与性命之诣深也;吾道者,其圣人与性命尽其圆极也。造端,圣人欲人知性命也;诣深,圣人欲人诣性命也;圆极,圣人欲人究其性命,会于天地万物,古今变化,无不妙于性命也”。“性命”成了儒佛道三者的共同理论基础。后来契嵩进一步研究了《中庸》,经过研究之后,契嵩发现“以《中庸》几于吾道”。
《中庸》是儒家经典,但契嵩以此来阐释和附会佛门性命之学,不能不说是一大创造。契嵩言:“若《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是岂不与经所谓‘实性一相’者似乎?…又曰: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尽人之性则尽物之性,以至与天地参耳’。是盖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岂不与佛教所谓万物同一真性者似乎?”
契嵩混佛于儒又通儒于佛,为宋代佛学儒学化铺平了道路。可见以契嵩为代表的一代僧侣在佛教儒学化过程中,从当时儒学中吸收了养分,这是宋代佛儒融合的历史趋势,也是宋代文化兼容精神的充分体现。
以上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侵权立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