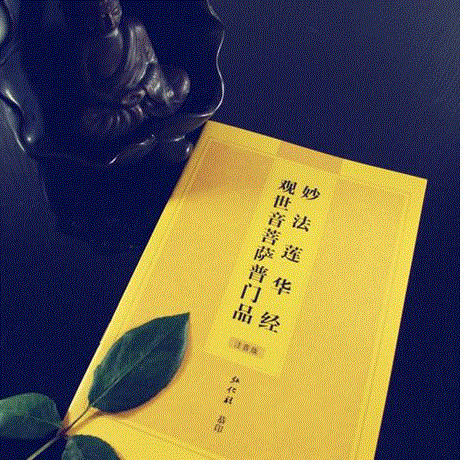季羡林:其学问“在中西之间”
发布时间:2024-10-26 03:04:47作者:普门品全文网学问在中西之间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与中国的东方研究 季羡林季羡林先生走了,走的时候虽然已是高龄,依然让人感觉突然。在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史上,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季羡林先生都可以称得上是最杰出的学者之一。
纵观季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涉及颇广,很难用一两个词语或者某一两个学科的名称来加以概括。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总结,中西之间四个字或许可以说明他的学问范围。

季羡林先生1935年赴德国。在德国期间,季先生发表了两篇论文:《〈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诸异本》(《德国东方学会学报》,1943);《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哥廷根科学院学刊》,语言历史类,1944)。在第一篇论文里,季先生利用不同语言,包括汉文中同一本生故事的各种文本,对吐火罗语的语词、语意、故事传译中的变化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吐火罗语及其文献的研究,对了解古代民族的迁徙和融合中西文化的交流,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一研究课题,正可说处于中西之间。第二篇论文则是讨论古代印度西北方言的语言特点。由于印度古代西北方言在早期佛教典籍的传播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其流行的地域又与中国新疆连接,研究这种语言的特点和它在民族迁徙、文化交流上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此外,季先生1949年在德国发表的《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判断佛典的年代和来源的标准》(《哥廷根科学院学刊》语言历史类,1949)一文,实际上也写成于这段时间。这几篇论文,在研究印度中世语言、尤其是佛教语言的学术界,几十年来,一直作为重要文献被引用。从这几篇论文可以看出,季先生从事研究的重要特点,是在掌握多种语言的基础上,从分析语言特点入手,结合其他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同样的论文,还有1947年直接用德文在《华裔学志》上发表的《巴利文的 A siy ati》。上面这几篇论文,如果说从大的学科划分而言,还在印度学的范围内,那么,季先生后来所作的研究、发表的论文,就不囿于印度学,而更多地涉及中国,更多地显示出中西之间的特点。这样的局面,也可说是客观的情形使然:首先,古代印度,作为南亚文明的发源地,在文化上与东亚的中国有极多的接触,中印文化交光互影,例证比比皆是。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到了中国,在中国后来有了极大的发展。中印两大文明古国,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互相学习,互相交流,这在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其间有很多值得认真研究的题目。季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的老师、学术界公认为一代宗师的陈寅恪先生自德国返国后,在清华任教的最初10年里,对这一方面的问题也非常注意。季先生在治学的门径、方法以至兴趣上,明显受到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在中印两大文化之间,陈寅恪先生尤其注意二者之间的中间区域,即中亚地区古代不同民族、语言、宗教之间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关系。季先生从一开始就极为服膺陈寅恪先生在这方面的见识,他在德国学习的虽然主要是印度和中亚的语言,但研究的对象和使用的材料却大量来自中国古代翻译的佛教典籍。他在涉及中国的学问方面,原来就有很好的基础。从研究印度和中亚的古语言、佛教的典籍,更多地转到与中国有关的题目上来,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当然,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国内,要继续完全从事印度和中亚古语言的研究,客观条件(如最重要的图书资料)与欧洲的德国相比,相差太远。季先生因此把研究的方向,更多地转向梵汉比较,或是与中印文化交流有关的题目。他把这种情形开玩笑地称作是有多大饭碗,吃多少饭。自然,先生也并未完全放弃对梵文的研究。
1946年春,根据国内的情形和客观条件,季先生很快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题目作了调整。到北京大学的第二年(1947年),他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了《浮屠与佛》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季先生充分利用了自己在印度和中亚古语言方面的功底和娴熟于各种佛教佛典的长处,对汉文中佛与浮屠(佛陀)两个译名的来源、出现的先后作了细密的考证。佛与浮屠二名的来源,表面看来细微末节,实际则反映出与佛教在中国最早传译的过程有关的诸多重要问题。这篇文章,由小而见大,见微而知著,发前人之未发,体现了季先生研究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