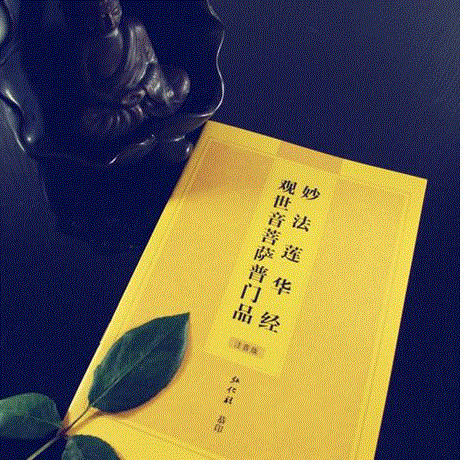佛光·山色·文化——峨眉山佛教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发布时间:2022-04-13 10:45:11作者:普门品全文网佛光·山色·文化——峨眉山佛教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张文良
峨眉山不仅是秀甲西川的风景区,更是具有特定历史及文化内涵的文化区。峨眉山文化源远流长,意蕴丰富,而绵延不绝以迄于今且蔚成大观的是佛教文化。以普贤菩萨信仰为核心的佛教文化构成峨眉山文化的主体和主流。文化不是死的,而是活的,这不仅指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开放的、发展的,而且指从根本上讲,文化是人的文化,是人的活动和人的思想,文化景观不过是附着于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峨眉山这一文化景观同样是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心灵和精神在峨眉山这一自然物上的外化和物化。分析这一文化景观,我们可以找到峨眉山文化起源、扩散和发展诸方面的证据,并可通过研究这些证据,更好地规划和发展过去的人们给自然所带来的变化。
峨眉山佛教文化的形成
就佛教义理而言,普贤是法身示现,示迹众影像,普人众法界,遍一切处又不住一切处,即是说普贤菩萨与文殊、观世音等众菩萨一样,随其应度而现化身,所以对普贤菩萨来说,时时在说法,处处是道场。但这是就其本地风光而言的,就世法而言,则普贤菩萨垂迹西川,现身峨眉,时至今日,峨眉是“普贤道场”早已成为佛教信徒普遍的信念。那么峨眉是怎样成为法缘福地的呢?
一些佛门弟子引《华严经·菩萨住处晶》的说法:
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与其
眷属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再根据峨眉昼有“佛光”,夜有“圣灯”,光明常住,且位居国土之西南,于是认定佛经所言光明山即峨眉山,贤胜菩萨即普贤菩萨。建于宋代的万年寺无梁殿,除供普贤菩萨外,还在殿之四壁层台上供小佛3000尊,寓意“眷属三千人”,就是根据这段经文而设。这种说法能否成立呢?先不讲《华严经》所言之西南不同于中土之西南,但就贤胜之名而论,遍查佛典,普贤菩萨有译为遍吉者,有说其过去世为泯图王子者,而未闻有贤胜名者。以贤胜为普贤,以峨眉此附《华严经》之光明山,显然只是一些人“欲借重经言以见重”,实不足为据。
但中国僧人所撰的《杂花经》却是值得注意的,这部经云:
诸佛以来,以大悲心为体,故用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而生菩萨心,因菩萨心
而成正觉。故我世尊正觉而有方所,说经而有道场。普贤于道场等门化人天等众,现相
海于峨眉山中,密引世人而通菩提觉性。《杂花经》属伪经是无疑的,但伪经不等于无价值,实际上它表达的内容虽然是杜撰的,但这“杜撰”本身却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僧众的心态,即希望普贤菩萨止住峨眉,兴慈运悲,佑护众生。西天佛国毕竟太遥远了,普通信众希望在中土也有普贤菩萨的说法道场。随着佛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以及普贤菩萨影响的扩大,确立普贤菩萨的说法道场,对宣扬普贤圣德,吸引更多的信众皈依佛教就显得尤其重要。普贤菩萨止住中土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然,至于普贤何以示迹“峨眉”而非三山五岳,则是一个文化发生学的问题。
据载,峨眉山开山建寺肇始于东晋隆安三年(397),是年,山僧建殿供普贤菩萨之像,并取名普贤寺。至于山僧为何专供普贤像,进而以普贤之名命名寺宇已不可考,但这一看似带很大偶然性的选择却成为峨眉之为普贤道场的最原始的根据。以后信众的种种说法、种种设置不过是强化了这一信念而已。在文化发生学上,最初带有偶然性的选择一旦作为既定的观念流传开来,就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显示某种必然性,发展到后来,这种观念变成人们普遍接受的信念,其原始的根据反倒被人们所忽略,如在民俗方面,冉有(伯牛)被奉为牛王,颜真卿(鲁公)被奉为豆腐王,杜甫(拾遗)被奉为女性土地杜十娘等,都是匪夷所思,但在后世却被相当多的人所接受。当然普贤之于峨眉与此不同,峨眉成为普贤道场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不是靠偶然的原因所能解释得了的,但在最初的发生机制上,它们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
在确立峨眉“普贤道场”地位方面,峨眉僧众居功实伟。东晋的普贤寺之后,峨眉僧众广建寺宇,大小寺庙普遍塑普贤像,而且这些建筑和雕塑都充分突显“普贤道场”的特色。按照佛教的说法,普贤地位次于佛祖,一般都供在最后一殿,惟峨眉伏虎寺供于第二殿,万年寺则是设立专殿,清音阁、洗象池、雷音寺则把普贤与文殊同列为释迦佛胁侍,同供一台,合称“华严三圣”。除寺庙供奉普贤外,寺外还供有许多普贤“圣迹”,如“洗象池”、“普贤塔”、“普贤石”、“普贤船”等等,所有这些,一方面体现出僧众对普贤的特殊尊崇,同时又造成一种浓郁的佛教氛围,强化着人们对“普贤道场”的认同心理。峨眉僧众还以《华严经》,特别是《普贤菩萨行愿品》作为讲经说法的主要经典,大力宣扬普贤盛德,特别是宣扬普贤菩萨的弘大愿力,
于诸疾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伏
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
又宣扬普贤菩萨神通广大、法力无边,
悉能破坏一切恶趣,悉能远离一切恶友,悉能制伏一切外道,悉能解脱一切烦恼,所有这些,不仅增进了广大信众对普贤菩萨的崇信,而且也使峨眉山作为普贤道场的声誉远播。此外,僧人们还编织了许多佛教神话和传说故事,其中汉永平年间蒲公上山采药,得见普贤示现的故事最为着名。这些神话故事无论是否有事实根据,都反映了信众祈望普贤垂迹人间、佑护众生的美好愿望。这些故事的广泛流传更使十方信众对峨眉与普贤的殊胜因缘深信不疑。
在过去的时代,社会最高统治者也对峨眉山的佛教倾注了热情,最早的是唐僖宗(874—888在位)敕建黑水寺,赐额“永明华藏”,又赐住持慧通禅师袈裟及诸供器。之后历朝历代帝王对峨眉俱有敕赐,其中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五年(980)的敕赐别有意义。是年,嘉州(今乐山市)地方官以峨眉白水寺现祥云及丈六金身相奏,太宗以为祥瑞,于是遣使铸普贤大士像,于寺内供养,这尊铜像通高7.4米,重62吨,至今仍供于万年寺。宋太宗此举的特殊意义在于,峨眉山的普贤信仰由民间信仰变成了民间和官方共同信仰,峨眉作为“普贤道场”的地位得到了官方的确认。在封建时代,帝王作为最高统治者,其信仰选择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导向作用,如果说峨眉的普贤信仰最初是自发的,那么朝廷的崇信就使其具有了某种权威性,如果说原来这种信仰还具有区域的局限,这之后它就更具普遍性,信仰的覆盖面更广。皇室尊崇峨眉供奉普贤当然有其信仰之外的政治用意,但在客观上却扩大了峨眉山的影响,并使峨眉之为普贤道场获得了皇权的支持。
峨眉山佛教文化的展开
峨眉山作为普贤道场的地位确立后,它就成为十方辐集的信仰中心,普贤菩萨圣德的感召力和峨眉胜景的吸引力形成各地信众强大的向心力。“天下之仰慕名山者,莫不摩顶踵,息妄缘,闲关峻岭之一登”。与峨眉发生直接关系的大体可分为这样一些群体:峨眉山僧众,峨眉山附近的居士,外地参礼的僧众,外地的香客或游客,还有一个不稳固的群体即皇室。这些群体都有一种共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即都是佛教的信仰者,而且都不是把峨眉山单纯看成自然景物,而是把它视为普贤的道场、朝礼的圣地。这种共同的信仰及相近的行为方式构在他们对峨眉这一给定景物相近的感应方式。但这些人和群体由于不同的身份、社会地位、不同的文化背景及由此所决定的不同的价值取向,他们面对峨眉这一自然景观又有相当不同的思想或情绪感受,所有这些又决定他们不同的行为动机以及在峨眉山文化建构方面不同的地位。
西晋初年即有云游僧人于峨眉结茅修行,之后一些僧人或云游至此,或闻风而来,到唐代,来山修行的僧人已达一定的规模。这些僧人或建寺宇,或启道场,或注经典,成为弘扬峨眉山佛教文化的中坚力量。在物质文化层面,僧众修建了大批寺庙,这些寺庙或建于山梁之上,或筑于幽谷之中,或悬于绝壁之畔,备极壮丽,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观。其代表性建筑有白水寺无梁殿、伏虎寺、报国寺、雷音寺、清音阁、遇仙寺、金顶华藏寺等等。峨眉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施工条件恶劣,修建寺宇并非易事,虽有皇室或显官大吏的支持,也往往费时长久。如清顺治八年(1651)贯之和尚主持修建伏虎寺,此寺占地百亩,殿堂十三重,依坡而上,历20年始竣工。其间贯之和尚及具体主其事的可闻和尚“朝昏竭蹶,鸠工庀材,继以规矩准绳”,筹量规划,不惮其劳。此外,僧人还造桥修路,植树造林,美化了峨眉的自然环境。如今我们看到的琼宇绀殿、山林景物,无不凝聚着先代僧众的辛勤努力。如果说峨眉是一座文化公园,那么峨眉僧众则是辛勤的园丁—。
应该指出的是当地的善男信女及护法居士,既包括督抚大吏也包括贫民百姓,为这些寺宇殿堂的建设也都出了大力。《可闻禅师塔铭》在谈到伏虎寺的建设时说“悉赖本省文武护法宰官捐金布施,檀那善人,共襄盛举。”他们不仅是僧众的布施者,而且是大批佛教建筑的实际建设者,许许多多无名的工匠和建筑师以自己的劳动表达出对佛及普贤菩萨的至诚/\
四川佛教分住山、住持部二部,住持部又分丛林系、诸山系,峨眉山寺庙就属于住持部丛林系。在唐代峨眉山就出现了多种宗派,发展到后来,影响最大的是临济、曹洞二宗,唐懿宗年间(859—872),蜀地眉州昌福和尚朝礼峨眉,并修建华严寺,招徒授道,阐扬临济宗风,是为临济宗峨眉立宗之始,其后承续临济法脉的高僧有唐慧通禅师、宋继业大师、明宝昙和尚等。清初“禅门世匠”破山大师于顺治十二年(1655)来山,与伏虎寺住持贯之和尚建“学业丛林”,招徒授道,举扬宗风,使万年寺、金顶、报国寺得以中兴。
峨眉山曹洞宗的开山祖师为唐澄照和尚。和尚亦于唐懿宗年间来峨,其后有明茂真和尚、无穷和尚、妙峰和尚等高僧来山,传承法脉。峨眉“金顶”即由妙峰和尚所建。除峨眉外,妙峰和尚还建有文殊、观音等金像并铜殿,万历皇帝誉之为“真正佛子”。
临济、曹洞同属慧能南宗一系,但由于门庭设施不同,特别是由于接引学者的方式不同,形成不同的门风。法眼宗的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称:“曹洞则敲唱为用,临济则互换为机。”这种不同只是说法接人的风格不同,其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即都是建立在理事圆融的基础上,如曹洞讲禅法的语句是偏正回互——他们有五位之说,即以偏正来讲,偏代表事,正代表理,互相配合而构成五种形式,即五位。所谓“敲唱为用”即是说明他的五位之间的相互配合,诸如偏中正、正中偏等各不相同,因而有唱有敲,于中听出他们的偏正来。临济则以宾主来代表理事,宾即事,主即理,不过宾主在说话中可以互换位置,如宾中主,主中宾,地位可以互换,问题在于听者能否知道这种情形。如:
有僧问昌福和尚:“如何是密室中人?”答:“昌福。”有人问曹洞僧澄照和尚:“诸佛有
难向火焰里藏身,衲身有难,向甚么处?”答:“小晶石上起波文,大地衲僧,都在里许。”又
问:“云何是初生月?”答:“大半人不见。”后人评临济、曹洞两家一为“触目是道”,一为“即事而真”,一家细密,一家痛快,由上面两则公案,亦可窥见其宗风之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峨眉僧众,无论属临济,还是属曹洞,都是教禅双修。许多禅宗高僧精研教理,契悟颇深。如唐大历十一年(776)来礼峨眉的澄观和尚发愿注疏佛经,后新译《华严经》,又作《普贤行愿品疏》,赠送峨眉山僧。昌福和尚亦尊奉《华严经》,修建华严寺,常诵《普贤行愿晶经》。澄照禅师亦精于佛理,每日六时朝拜普贤大士。峨眉僧众尊奉《华严经》,常礼普贤,不仅因为他们所止住的普贤道场,而且禅本来就与《华严》教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禅完全建立在《华严》理事圆融基础上,禅宗各派不过是用不同方式来表现这一中心而已。临济重视从主观方面来体会理事的关系,由理的方面体现到事,也就是说,以理为根据来见事,所以所见者无不是道;曹洞则把重点摆在事上,注重客观,在个别的事上体会出理来。峨眉禅师修禅不废教,使其禅会通教义而发,避免了凌空而谈、不着边际的口头禅之弊,可以说是禅法的正脉。
峨眉僧众的另一优良传统是讲求真参实证。普贤菩萨以其随/顷众生等十大行愿赢得“愿王”或大愿菩萨的称号。《行愿品》中有一段经文:
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
慧华果。欲涉普贤境界,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修得大誓愿、大精进、大智慧,证得菩提觉性,才能得普贤菩萨印证,人大光明藏海。
晋代名僧慧远之弟慧持曾于峨眉说法度众,一生持戒谨严,道风远播,临终为弟子
留言:“经言戒如平地,众善由生,汝等行住坐卧,宜其谨哉!”后世峨眉僧众正是准此而行的。明代通天大师出家后以十事律身:

誓愿悟道,誓同净戒,誓不攀援,誓目不视美好,誓滴水同饷,誓肋不着席,誓不慢后
学,誓不畜余物,誓修净土,誓老不改行。在几十年修道生涯中,大师信守誓言,终身无遗在云游天下、遍参善知识的途中,或作头陀于树下,或卧幽壑深林,或坐险崖古洞,数十年间方了却大事,得法自在。又如明妙峰禅师,幼而颖悟,闭关修禅观未久即有悟处,作偈呈山阴王,王为挫其狂气,寄一破鞋底并一偈与妙峰,云:
这片臭鞋底,封将寄与汝,并不为别事,专打作诗嘴。妙峰接得,以线将鞋底系项,一心闭关,三年关满,本分事明。明代破山大师与贯之和尚创立学业禅堂,就是有感于教禅律流,各执一边,鲜能知体达用,三法共行,故望通过整顿丛林,以养育贤才,陶铸后学,其用心可谓良苦。
峨眉山佛教文化的传播
峨眉山的僧众及护法居士是使峨眉佛教文化蔚成大观的核心力量,但使峨眉山名播宇内,并使其影响辐射开来,却主要是外地僧人及香客的贡献。
据《峨眉山志》载,唐玄奘在西行求法前曾登峨眉礼普贤参师求道,据说在九老洞一老僧授以佛经一册并佛偈四句:
汝般若舟,慈悲度一切。普贤行愿深,广利无边众。玄奘感悟,坚定了弘法利生的信心。密宗第五代祖师柳本尊,于唐光启二年(886)冬,登峨眉山礼普贤光相。时值大雪封山天寒地冻,为表礼佛之诚,他从早到晚坐于雪中,默诵经文,受到僧众的敬重。十方朝礼的僧众,人山而瞻相好,睹瑞光,心灵即能得到一次净化和升华,峨眉不仅是神圣的道场,更是一大选佛场。
因为峨眉主要是禅宗道场,故外地禅宗高僧大德,大多不辞辛苦,千里来参。
唐代赵州从谂禅师礼峨眉,上放光台,不登宝塔顶,有僧问:“和尚云何不到至极
处?”谂云:“三界之高,禅定可入,西方之旷,一念而至,惟有普贤,法界无边。通常人们皆以超出三界,往生西方为期,而赵州禅师则认为其实这并不难,难的是立普贤愿,行普贤行,因为普贤之愿广大,其行无边,所以圆满普贤行愿,不是常人所能企及。赵州的法语,既表达了禅师对普贤圣德的崇奉,也表达了禅师对佛教根本精神的深刻契悟。
唐黄檗希运礼峨眉,至睹佛台,雾气澄霁,曰:“云何不见?”僧问:“不见甚么?”云:
‘\‘不见普贤。’\’赵州、希运等禅师都是即物发凡,随机说法,表现出很高的境界,而峨眉的自然风物则成为逗发其禅机的灵感之源。
外来的香客是传播峨眉佛教文化的另一重要力量。在过去交通不便、山水阻隔的情况下,欲亲礼峨眉山实非易事,能不惜艰险,登上峨眉者必是深具信心、久蓄弘愿的信士。这些香客既有内地的汉民,也有西藏的教民,既有文雅士,更多的是普通百姓。这些香客在峨眉进香礼佛,布施僧尼,在诵经梵呗声中,净化了心灵,加深了对佛教的情感,而亲睹金顶祥光、“普贤圣灯”又会激起香客美好的遐想,留下终身难忘的回忆。对那些文人雅士而言,峨眉雄伟壮丽的自然景观,激发其艺术想像力,浓郁的佛教文化,激发其艺术灵感,而超凡脱俗的精神氛围,又赐予其空灵澄澈的创作心境,他们的成就表现在诗文书法各个方面,尤其是诗文,无论是否是名家的作品,都给人以清新、洁净、恬淡、和谐之感,并时时折射出禅光佛影。如李白《听蜀僧浚弹琴》: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音入霜钟。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既有李白式的豪迈奔放,又有佛教的象征意味。杜甫久居成都,然因战乱,未曾登临近在咫尺的峨眉,后人莫不引以为憾,但他还是留下了与峨眉有关系的诗篇,如《漫成》:
江皋已仲春,花下复清晨。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
近识峨眉老,知余懒是真。平淡自然而神韵超逸,空明谧静而又灵动圆满,虽非谈禅而有禅趣。又如苏轼《寄眉峰》:
胶西高处望西川,光在孤云落照边。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治经方笑
春秋学,好士今无六一贤,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趋流年。其疏阔放达之情怀与山水景物融会在一起,清秀灵异,迥出常格。这些动人的诗篇既给人以美的享受,又会使读者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它们与峨眉山珍藏的历代名家书画作品一道,构成峨眉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它们作为精神文化,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所以其影响比之其它文化形态可以传播得更为久远。这些诗篇的广泛传诵,激起了人们对峨眉的美好想象,也激发了人们对峨眉的向往之情,这就大大提高了峨眉作为天下名山的知名度,也提高了峨眉作为“普贤道场”的声誉。
结语
任何宗教都是一种群体现象,任何宗教文化都具体表现为特定社会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峨眉山佛教文化同样是活生生的人的思想、人的行为的外化和物化。人们指向峨眉山的思想和行为首先是一种选择,最初开山者认定此处为“普贤道场”也是一种选择,不过前一种选择带有偶然性,而后者则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选择,带有更多的必然性。经过世世代代的僧众、护法、香客的惨淡经营,才有了今日的峨眉山,而峨眉山独具的文化品格作为一种传统,又构成我们今天选择的前提和背景。今天我们要开发建设峨眉山,首先应该从人文角度来评价峨眉山的资源条件及其意义,即首先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文化因素特别是佛教文化是形成该区域特性的关键因素,应该把人文因素的开发利用看成实现峨眉发展目标的首要途径,这就必须加强对峨眉山佛教文化的研究,这不仅对开发峨眉山有特殊要的意义,而且可以更好地对游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