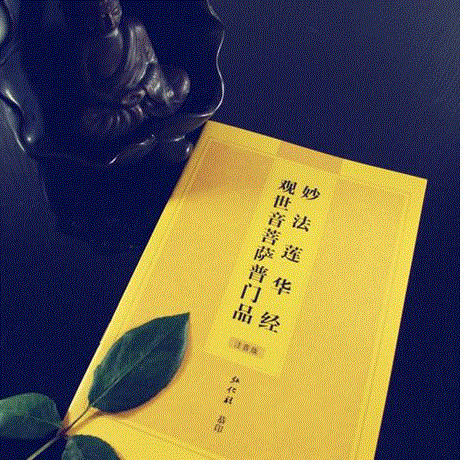四川妙音:我的信佛因缘
发布时间:2024-07-15 03:02:45作者:普门品全文网
四川妙音:我的信佛因缘
我不知道家族中其它家庭是否和我们家一样,在只有书信往来的年代,只要一收到爷爷寄来的信,就要开家庭会议,首先当然是宣读爷爷信中的内容,而每封信都是让我们好好扎根边疆,以及党中央的新精神,叮嘱我们一定要把精神落实在实处,跟着党的路线走……。
在爷爷的影响下,他的子女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成为很杰出的人,当然,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第一次和无神论者的接触
第一次听到鬼神异说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一家人都能看到鬼,他说,当他属羊的哥哥由于意外pass away时,当晚他家所有的人都梦见:一头落泪的白羊被一个白胡子老人牵着,“咩咩”叫着,一步一回头的走了;还有他的母亲有一次住院时,在夜色中看见一个背对着她的女子,坐在电脑前打字,她母亲是一个文盲,至于“电脑”一词也是在给儿子描述这一见闻中被告知的。这些如聊斋般的旧事,在使我感觉新奇的同时,也使我产生了困惑,世上真的有鬼吗?
处于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在当晚睡时,我许下了一个令我后悔很久的愿望:如果世上真的有鬼就出来吧,让我也见识见识。于是在当晚我睡着后不久,伴着窗户发出的响声,及床边地面上的风声,我似乎醒了,但眼皮如沉重的闸门,怎么也张不开,在少许恐惧下,我试图伸手打开床边的灯,但手却好象被人抓住了,这时的我,真觉得恐怖万分,想喊也喊不出来,情况持续了几分钟,后来我好象又睡着了,再醒来已是清晨,我很想以为那是一个梦,但那梦却如此清晰。在我向外人提及时,也有人告诉我说那是梦魇,但以前我为什么从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而在我无知的许下如此愚蠢的愿望后,就有了如此的经历,这真的是巧合吗?反正这件事着实使我毛骨悚然了一回。
我的大学生活
然而真正使我的思想发生质的转变是我在内地上大学的时候,:(我相信,我的父母如果知道为了提高我的独立生活能力,把我送出去上大学这一决定的结果是:使我成为一个有神论主义者的话,他们一定会选择把我留在身边读书,那样我就真的与学佛无缘了:),事实上直到现在他们还在困惑:象我们这样的家庭怎么会教育出象我这样一个“异类”?!这无疑使他们感觉到有这样一个女儿是他们教育事业中的重大失败(他们是同一所大学的院长和教授)。
毫不谦虚的说,我的大学生活是在严谨、有秩序、有规律、刻苦攻读中度过的,那时我还是个一心想着努力学习报答父母的天真执著的小女孩。也许是对我努力学习的回报,我被选为班上的学习委员。
那个学期我们有一门课是电路基础,上课的老师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人,也许是年青人在一起比较谈得来,在一次谈天中他告诉我这个地方很斜门,有一次他明明是关上了灯睡觉,可是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却发现灯开着,在我惊讶的目光中,他一脸诡异的说:“因为这里以前是城隍庙,后来推了在上面建了这所大学,所以这里奇怪的事不断。”于是我开始留意一些同学们的议论,结果令我大吃一惊,原来真的有那么一回事,甚至我旁边那张床上下铺的人,经常抱怨他们的床每天半夜总在摇晃,也找到了真正的原因,事实上好象除了粗心的我,一切人都先后知道了这个“事实”——这里闹鬼。只是大家心领神会而已。
据老生们说,这里流行一种叫“出血热”的病,据说是由老鼠传播的,一开始发病时很象感冒,如果吃西药就会使人全身毛细血管脆裂而死;而且我们这届新生住的地方,每年会有“一死一疯”,我不知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把这话当作了荒谬言论,继续我紧张而充实的学习生活。然而,这个“传言”在以后的日子中,却得到可怕的证实。
关于“一死一疯”的预言
孙斌是内蒙人,白里透红的四方脸,大刀眉,一脸的稚气,写得一手好字,我对他的好印象缘于第一个寒假。那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冷,在火车站候车室,我和同乡们每人都提着大包小包,也许是被将踏上回家旅途情绪的感染,我们每个人都好象容光焕发,笑的也格外开朗。时间的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流逝,终于开始检票了,仿佛在黑暗及漫长的等待中见到了一丝曙光,人们象疯了一般飞步向火车停处跑去,我掉队了,原因是由于缺乏经验,我的行囊过于沉重,几乎每迈一步都要靠膝盖来带动,男生们已在前方去占行李架,茫然、无助、焦虑把先前的好心情冲刷的荡然无存,路是那么长,腿是那么沉,你一定可以想象,当一双强有力的手并伴随“我来帮你”的话语,接过我的包时,我是多么的温暖和感激。从简短的谈话中,我得知坐明天火车的他是专程来送我们的……。
当带着寒假的愉悦再次返校时,我已被评为学习委员了,这虽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可管的事情就太繁多了,除了一般的交 作业,组织教师和同学间的交流会,布置学习园地、试前写考号外,还有管理班费,夜晚查铺等与“学习委员”一职毫不相干的任务。鉴于他的特长,我总是让他帮我写考号,到银行存班费时(大概有一二千元吧),又让他充当保镖,而他总是笑着无条件的帮助我,我们的友情就在这一点一滴中 增长。转眼间,又一个学期即将结束,考试后他来找我,带着我熟悉的笑容和真诚,请我帮他同乡(考场作弊被当场抓获者)开脱,让她补考而不是处分……。
接下来的暑假是在兴奋与忙碌中度过的,当我满面春风又回到校园时,迎接我的却是一个出奇不意的消息:孙斌得“出血热”死了!他的同乡说:“病是他在学校得的,回家后,从他发病到死也就是一个星期的事”。我的心一下子被这闪电般的袭击打得粉碎,泪水无声的划过我的面庞……。
死神就是这样,在我们视生命为理所当然时,带着狰狞的微笑,在毫无警示的情形下悄悄到来,它庞大的身影使我们感到,平时所计划、操心、计较的一切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毫无意义……。
至于那个会有一个疯子的预言,也不幸的被言中,不过,她不是我们班的,所以,我没有对她留下太深的印象,但说来也巧,刚入校时,我们曾分在同一间宿舍,那时的她看来和平常人没有什么不同,由于我们学的不是一个专业,后来就分开了,快毕业时,听人说她疯了,我自然不信,直到有一次,我在洗脸间遇到她,她目光呆滞,还不停的自言自语,看来,是真有其事了。这一切在让我落泪与惋惜的同时,也令我深切的体会到世事无常的哀凉。
南五台之行——第一次与净土结缘
在紧张的学习生涯中,最令人兴奋的没过于去爬山郊游了,一个清朗的早晨我们有组织的穿过田野,越过小溪,扑入大山的怀抱,新鲜的空气,鸟儿的吟唱,太阳暖暖的照在我们身上,微风亲密的吹袭着脸庞,一切都是那么美丽而和谐。
在我们爬到山中腰时,发现有一大队人都手拿念珠,合掌而行,他们并不说笑,连交头接耳也没有,只是垂着眼帘,嘴唇微动,念着“阿弥陀佛”,一个接一个向一座寺院走去。处于好奇,我们也跟着进去凑热闹。
这是三个深红色飞檐式的木房围成的小寺院,中间仅有的一块空地已站满了类似我们刚才所见的人,一辆天蓝色的拖车拉着半人高的大纸箱,停在中央。这时,前面到的同学说,车里有免费的东西吃,顿时提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穿过人群,我们走了过去,看见一个慈祥的老太太,手中拿着白色的布兜,正在给同学们分着花生和饼干,我们也被分到一些。当我们正热衷于瓜分得到的食品时,那大纸箱已不知在何时,被抬下车放在了中间那个木房前,十几个红衣僧尼,围着纸箱念起经来,其中有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的女尼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的脸圆润而光洁,在众人的围观下,她有些紧张,水灵灵的大眼睛,不时瞟着我们,我当时在纳闷,为什么如此年青的女子会出家呢?因为那时我以为看破红尘或受到什么重大打击,而无法平复的人才会出家。这时,无缘由的,我又感知在纸箱中的一定是一个七、八十岁,盘着腿的女尼,一想到刚才所吃下去的东西是因她而得,顿觉十分的不自在,也许其它人也有同感,我们不约而同的认为应该继续爬山。
事实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这是一段倒霉的经历,后来就渐渐淡忘了,直到我接触净土宗时,偶然回想起来,才领悟出它的美妙、庄严与殊胜。
我的先生(sir)
我和我的先生其实在上大学以前就有过一面之缘,他是由我家的世交,汤阿姨带来的,当时是我先生的班主任,sir戴着一付黑色框架的睛镜,显得文质彬彬,汤阿姨说:“他和你考上了同一所大学,学得也是一个专业,你们可以认识一下。”我礼貌的点了点头,大概是我不善于和陌生人一起交谈,过了不久他便告辞了。这次见面并没有使我对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到了学校后,对新环境适应和严谨的学习生活使我们形同陌路,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第二学期,我当上学习委员。说实话,这是份劳心劳力又得罪人的差事,而且不能为此而耽误学习,如果那样就名不副实了。
某日,当我看着别人用心读书,而我不得不职责所在的,按领导的要求修饰教室后的学习园地时,委曲象一缕青烟,从心底那柔软的角落慢慢升起,让我有些想哭了,就在这时,sir不失时机的走了过来,帮我一起工作,这一举动,令多愁善感的我感到很温馨,由此开始对他产生了好感。他的课余生活几乎都花在学习上,而我身边的朋友们,却走出教室就再不想回来,更吸引她们的是打毛衣和闲聊。相同的爱好,使我和sir产生了共同语言,在无数次的学习探讨中,我们的友情不断深厚。也开辟了新的话题,从而得知他们宿舍中有两个人(哲和辉),已被一位修文殊法的密宗女居士收为弟子,经常在夜晚息灯后打坐,其实,在sir告诉我以前,我对此事也略有所闻,因为也同时收了我们班的两位女弟子。据说,他们前世曾在同一寺院修行,我想他们前世一定是男子。哲和sir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告诉sir,他的上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修行人,能知过去未来,他的弟子全国各地都有。由于他很少和上师见面,哲的师父录了一盘磁带(据说是经文),哲很珍惜,在打坐时才很小心的拿来听一听,然而这盘带子竟然被一个毛手毛脚的家伙(皓)给洗掉了,哲当时就预言说,这会给他俩带来一些灾祸,果不其然,不久后哲就丢掉了一份“美差”,而皓却因“犯事”被开除了学籍。
经常的耳濡目染使sir的好奇心驱使他萌发起想见这位神秘人物的愿望。这种梦想在他快要毕业时得已实现,这次见面他们谈论了sir的前世,以及毕业后的工作去向。她还嘱咐说要经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当sir想要拜这位居士为师时,她却平和的说:“你的师父另有其人”,这无疑使sir感到很遗憾。
后来,sir 带着神秘的表情告诉了我这件事。如果说当时我们对这位高人所说的话,还有些许疑惑,那么毕业后,我们的境遇和预言所说的一丝不差,就使我们彻底成为一个有神论者。
与净土再续前缘
从毕业到九八年九月,我们都是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中度过的,当然,我和sir也结婚了。一次偶然的机缘,我们得到了净空法师于八八年在新加坡讲解的《无量寿经》录音磁带,顿时,心中欢喜万分,我们决定如法修行:吃素、念佛、布施、持八关斋戒、过午不食,不看电视、报纸。我们从网上下载并认真听了所有净空法师的音像文件,还刻成光盘发送。如此种种,当然那时的念佛是恳求,求佛千万要救我,念佛时也比较紧张,用最大的气力,念得满身是汗,才觉得念得有些成效,如此精进,也得到了佛力最大的加被。终于,一九九九年四月,在会纯师兄的“永恒生命的呼唤”网站上读到圣苏法师的《本愿念佛讲话》,我们才彻底的理解了佛的无条件救度,才懂得了佛的大慈大悲。从此成为“不断烦恼得涅槃,真实纯情的念佛人”。
怀着感恩的心情,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分享我们的喜悦,在弥陀的怀抱中,早日得到大安心、大满足。在sir的全力支持下,一九九九年十月,蒙佛加被,“回归家园”网站诞生了。
“同一念佛无别道,远通四海皆兄弟!”,愿有缘众生,同沾法喜,同生极乐。南无阿弥陀佛!
很多次,有人问我:“妙音你是一个学电脑的,也算得上是高科技了,为什么会信佛呢? 我总是笑答“因缘使然”。在听者疑惑不解的目光中,我又一次开始了细心的解释……
我的家庭
也许你不信,我生在一个正统的革命主义家庭,爷爷曾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起义军官,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上山下乡的洪潮中,他主动把子女送到了边疆,当然后来爷爷也说,许多当官的,当时是想尽办法把亲戚、子女往京里调,可是他从不后悔,因为他认为:跟着党的路线走,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由于我们家太边远,我与爷爷没有见过几次面,不过我知道他老人家一定是一个很善良、很有原则的人,七八十岁了不坐专车,却去挤公共汽车,见了小孩或孕妇还主动让位,在他的心中,自己永远是年青的。

我不知道家族中其它家庭是否和我们家一样,在只有书信往来的年代,只要一收到爷爷寄来的信,就要开家庭会议,首先当然是宣读爷爷信中的内容,而每封信都是让我们好好扎根边疆,以及党中央的新精神,叮嘱我们一定要把精神落实在实处,跟着党的路线走……。
在爷爷的影响下,他的子女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成为很杰出的人,当然,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第一次和无神论者的接触
第一次听到鬼神异说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一家人都能看到鬼,他说,当他属羊的哥哥由于意外pass away时,当晚他家所有的人都梦见:一头落泪的白羊被一个白胡子老人牵着,“咩咩”叫着,一步一回头的走了;还有他的母亲有一次住院时,在夜色中看见一个背对着她的女子,坐在电脑前打字,她母亲是一个文盲,至于“电脑”一词也是在给儿子描述这一见闻中被告知的。这些如聊斋般的旧事,在使我感觉新奇的同时,也使我产生了困惑,世上真的有鬼吗?
处于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在当晚睡时,我许下了一个令我后悔很久的愿望:如果世上真的有鬼就出来吧,让我也见识见识。于是在当晚我睡着后不久,伴着窗户发出的响声,及床边地面上的风声,我似乎醒了,但眼皮如沉重的闸门,怎么也张不开,在少许恐惧下,我试图伸手打开床边的灯,但手却好象被人抓住了,这时的我,真觉得恐怖万分,想喊也喊不出来,情况持续了几分钟,后来我好象又睡着了,再醒来已是清晨,我很想以为那是一个梦,但那梦却如此清晰。在我向外人提及时,也有人告诉我说那是梦魇,但以前我为什么从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而在我无知的许下如此愚蠢的愿望后,就有了如此的经历,这真的是巧合吗?反正这件事着实使我毛骨悚然了一回。
我的大学生活
然而真正使我的思想发生质的转变是我在内地上大学的时候,:(我相信,我的父母如果知道为了提高我的独立生活能力,把我送出去上大学这一决定的结果是:使我成为一个有神论主义者的话,他们一定会选择把我留在身边读书,那样我就真的与学佛无缘了:),事实上直到现在他们还在困惑:象我们这样的家庭怎么会教育出象我这样一个“异类”?!这无疑使他们感觉到有这样一个女儿是他们教育事业中的重大失败(他们是同一所大学的院长和教授)。
毫不谦虚的说,我的大学生活是在严谨、有秩序、有规律、刻苦攻读中度过的,那时我还是个一心想着努力学习报答父母的天真执著的小女孩。也许是对我努力学习的回报,我被选为班上的学习委员。
那个学期我们有一门课是电路基础,上课的老师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人,也许是年青人在一起比较谈得来,在一次谈天中他告诉我这个地方很斜门,有一次他明明是关上了灯睡觉,可是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却发现灯开着,在我惊讶的目光中,他一脸诡异的说:“因为这里以前是城隍庙,后来推了在上面建了这所大学,所以这里奇怪的事不断。”于是我开始留意一些同学们的议论,结果令我大吃一惊,原来真的有那么一回事,甚至我旁边那张床上下铺的人,经常抱怨他们的床每天半夜总在摇晃,也找到了真正的原因,事实上好象除了粗心的我,一切人都先后知道了这个“事实”——这里闹鬼。只是大家心领神会而已。
据老生们说,这里流行一种叫“出血热”的病,据说是由老鼠传播的,一开始发病时很象感冒,如果吃西药就会使人全身毛细血管脆裂而死;而且我们这届新生住的地方,每年会有“一死一疯”,我不知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把这话当作了荒谬言论,继续我紧张而充实的学习生活。然而,这个“传言”在以后的日子中,却得到可怕的证实。
关于“一死一疯”的预言
孙斌是内蒙人,白里透红的四方脸,大刀眉,一脸的稚气,写得一手好字,我对他的好印象缘于第一个寒假。那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冷,在火车站候车室,我和同乡们每人都提着大包小包,也许是被将踏上回家旅途情绪的感染,我们每个人都好象容光焕发,笑的也格外开朗。时间的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流逝,终于开始检票了,仿佛在黑暗及漫长的等待中见到了一丝曙光,人们象疯了一般飞步向火车停处跑去,我掉队了,原因是由于缺乏经验,我的行囊过于沉重,几乎每迈一步都要靠膝盖来带动,男生们已在前方去占行李架,茫然、无助、焦虑把先前的好心情冲刷的荡然无存,路是那么长,腿是那么沉,你一定可以想象,当一双强有力的手并伴随“我来帮你”的话语,接过我的包时,我是多么的温暖和感激。从简短的谈话中,我得知坐明天火车的他是专程来送我们的……。
当带着寒假的愉悦再次返校时,我已被评为学习委员了,这虽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可管的事情就太繁多了,除了一般的交 作业,组织教师和同学间的交流会,布置学习园地、试前写考号外,还有管理班费,夜晚查铺等与“学习委员”一职毫不相干的任务。鉴于他的特长,我总是让他帮我写考号,到银行存班费时(大概有一二千元吧),又让他充当保镖,而他总是笑着无条件的帮助我,我们的友情就在这一点一滴中 增长。转眼间,又一个学期即将结束,考试后他来找我,带着我熟悉的笑容和真诚,请我帮他同乡(考场作弊被当场抓获者)开脱,让她补考而不是处分……。
接下来的暑假是在兴奋与忙碌中度过的,当我满面春风又回到校园时,迎接我的却是一个出奇不意的消息:孙斌得“出血热”死了!他的同乡说:“病是他在学校得的,回家后,从他发病到死也就是一个星期的事”。我的心一下子被这闪电般的袭击打得粉碎,泪水无声的划过我的面庞……。
死神就是这样,在我们视生命为理所当然时,带着狰狞的微笑,在毫无警示的情形下悄悄到来,它庞大的身影使我们感到,平时所计划、操心、计较的一切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毫无意义……。
至于那个会有一个疯子的预言,也不幸的被言中,不过,她不是我们班的,所以,我没有对她留下太深的印象,但说来也巧,刚入校时,我们曾分在同一间宿舍,那时的她看来和平常人没有什么不同,由于我们学的不是一个专业,后来就分开了,快毕业时,听人说她疯了,我自然不信,直到有一次,我在洗脸间遇到她,她目光呆滞,还不停的自言自语,看来,是真有其事了。这一切在让我落泪与惋惜的同时,也令我深切的体会到世事无常的哀凉。
南五台之行——第一次与净土结缘
在紧张的学习生涯中,最令人兴奋的没过于去爬山郊游了,一个清朗的早晨我们有组织的穿过田野,越过小溪,扑入大山的怀抱,新鲜的空气,鸟儿的吟唱,太阳暖暖的照在我们身上,微风亲密的吹袭着脸庞,一切都是那么美丽而和谐。
在我们爬到山中腰时,发现有一大队人都手拿念珠,合掌而行,他们并不说笑,连交头接耳也没有,只是垂着眼帘,嘴唇微动,念着“阿弥陀佛”,一个接一个向一座寺院走去。处于好奇,我们也跟着进去凑热闹。
这是三个深红色飞檐式的木房围成的小寺院,中间仅有的一块空地已站满了类似我们刚才所见的人,一辆天蓝色的拖车拉着半人高的大纸箱,停在中央。这时,前面到的同学说,车里有免费的东西吃,顿时提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穿过人群,我们走了过去,看见一个慈祥的老太太,手中拿着白色的布兜,正在给同学们分着花生和饼干,我们也被分到一些。当我们正热衷于瓜分得到的食品时,那大纸箱已不知在何时,被抬下车放在了中间那个木房前,十几个红衣僧尼,围着纸箱念起经来,其中有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的女尼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的脸圆润而光洁,在众人的围观下,她有些紧张,水灵灵的大眼睛,不时瞟着我们,我当时在纳闷,为什么如此年青的女子会出家呢?因为那时我以为看破红尘或受到什么重大打击,而无法平复的人才会出家。这时,无缘由的,我又感知在纸箱中的一定是一个七、八十岁,盘着腿的女尼,一想到刚才所吃下去的东西是因她而得,顿觉十分的不自在,也许其它人也有同感,我们不约而同的认为应该继续爬山。
事实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这是一段倒霉的经历,后来就渐渐淡忘了,直到我接触净土宗时,偶然回想起来,才领悟出它的美妙、庄严与殊胜。
我的先生(sir)
我和我的先生其实在上大学以前就有过一面之缘,他是由我家的世交,汤阿姨带来的,当时是我先生的班主任,sir戴着一付黑色框架的睛镜,显得文质彬彬,汤阿姨说:“他和你考上了同一所大学,学得也是一个专业,你们可以认识一下。”我礼貌的点了点头,大概是我不善于和陌生人一起交谈,过了不久他便告辞了。这次见面并没有使我对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到了学校后,对新环境适应和严谨的学习生活使我们形同陌路,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第二学期,我当上学习委员。说实话,这是份劳心劳力又得罪人的差事,而且不能为此而耽误学习,如果那样就名不副实了。
某日,当我看着别人用心读书,而我不得不职责所在的,按领导的要求修饰教室后的学习园地时,委曲象一缕青烟,从心底那柔软的角落慢慢升起,让我有些想哭了,就在这时,sir不失时机的走了过来,帮我一起工作,这一举动,令多愁善感的我感到很温馨,由此开始对他产生了好感。他的课余生活几乎都花在学习上,而我身边的朋友们,却走出教室就再不想回来,更吸引她们的是打毛衣和闲聊。相同的爱好,使我和sir产生了共同语言,在无数次的学习探讨中,我们的友情不断深厚。也开辟了新的话题,从而得知他们宿舍中有两个人(哲和辉),已被一位修文殊法的密宗女居士收为弟子,经常在夜晚息灯后打坐,其实,在sir告诉我以前,我对此事也略有所闻,因为也同时收了我们班的两位女弟子。据说,他们前世曾在同一寺院修行,我想他们前世一定是男子。哲和sir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告诉sir,他的上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修行人,能知过去未来,他的弟子全国各地都有。由于他很少和上师见面,哲的师父录了一盘磁带(据说是经文),哲很珍惜,在打坐时才很小心的拿来听一听,然而这盘带子竟然被一个毛手毛脚的家伙(皓)给洗掉了,哲当时就预言说,这会给他俩带来一些灾祸,果不其然,不久后哲就丢掉了一份“美差”,而皓却因“犯事”被开除了学籍。
经常的耳濡目染使sir的好奇心驱使他萌发起想见这位神秘人物的愿望。这种梦想在他快要毕业时得已实现,这次见面他们谈论了sir的前世,以及毕业后的工作去向。她还嘱咐说要经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当sir想要拜这位居士为师时,她却平和的说:“你的师父另有其人”,这无疑使sir感到很遗憾。
后来,sir 带着神秘的表情告诉了我这件事。如果说当时我们对这位高人所说的话,还有些许疑惑,那么毕业后,我们的境遇和预言所说的一丝不差,就使我们彻底成为一个有神论者。
与净土再续前缘
从毕业到九八年九月,我们都是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中度过的,当然,我和sir也结婚了。一次偶然的机缘,我们得到了净空法师于八八年在新加坡讲解的《无量寿经》录音磁带,顿时,心中欢喜万分,我们决定如法修行:吃素、念佛、布施、持八关斋戒、过午不食,不看电视、报纸。我们从网上下载并认真听了所有净空法师的音像文件,还刻成光盘发送。如此种种,当然那时的念佛是恳求,求佛千万要救我,念佛时也比较紧张,用最大的气力,念得满身是汗,才觉得念得有些成效,如此精进,也得到了佛力最大的加被。终于,一九九九年四月,在会纯师兄的“永恒生命的呼唤”网站上读到圣苏法师的《本愿念佛讲话》,我们才彻底的理解了佛的无条件救度,才懂得了佛的大慈大悲。从此成为“不断烦恼得涅槃,真实纯情的念佛人”。
怀着感恩的心情,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分享我们的喜悦,在弥陀的怀抱中,早日得到大安心、大满足。在sir的全力支持下,一九九九年十月,蒙佛加被,“回归家园”网站诞生了。
“同一念佛无别道,远通四海皆兄弟!”,愿有缘众生,同沾法喜,同生极乐。南无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