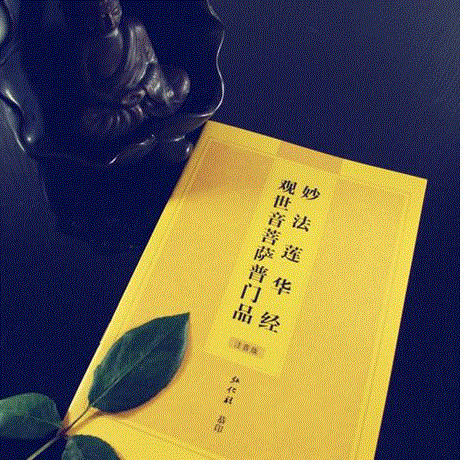三种佛性与真实胜乘——摄论师的佛性、一乘思想
发布时间:2023-07-06 09:43:44作者:普门品全文网三种佛性与真实胜乘——摄论师的佛性、一乘思想
圣凯
内容提要:摄论师继承真谛以真如诠释佛性的传统,而且将第一义空、自性清净心、阿摩罗识、解性等都纳入佛性的思想体系。而且摄论师逐渐背离了瑜伽行派的立场,而与“真常唯心”系合流,强调以佛性为中心,以“佛性”诠释“十胜相”,完全是以如来藏缘起来解读《摄论》,这是摄论学派中国化的核心体现。同时,摄论师将真如、理等同起来,以诠释“本有”佛性的普遍性、内在性,依此而批评新译唯识的“无性”与“少分”;依三种佛性说“亦本亦始”,并依此而批评新译唯识“理性平等,行性差别”。摄论师依佛性解释“究竟一乘”,完全是真常唯心的思想。
真谛在不违背瑜伽行派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提出“一性皆成”与“究竟一乘”,从而建构了摄论学派的佛性思想。真谛之后的摄论师,由于受到北方佛教的《十地经论》、《涅槃经》的影响,更加努力去重建与弘扬本学派的佛性思想。而且,逐渐偏离了瑜伽行派的立场,而融入当时中国佛教界的“主流”真常唯心思想。另一方面,唐初摄论师接触新译唯识的“五性各别”,便对其进行批判,高举“一性皆成”的旗帜,于是便出现唐初佛性论争的局面,其代表人物有灵润等。[1]
但是,研究摄论师的佛性思想,现存文献资料极其有限,日僧最澄《法华秀句》卷中,曾记载灵润“造《一卷章》,辨新翻《瑜伽》等与旧经论相违”[2],这是比较集中的文献。敦煌遗书中的《摄论》章疏有关佛性部分,都没有保存下来。另外,便是隋唐论著中的零星记载。所以,我们必须综合这些零碎的资料,而对摄论师的佛性思想进行整体性的诠释。
一、三种佛性与正因佛性
真谛以真如诠释“佛性”,建立应得因、加行因、圆满因三因佛性,应得因本身又具有三种佛性——住自性性、引出性、至得性。摄论师在真谛的三种佛性的基础上,又作出新的诠释。尤其是对佛性本质的探讨,即“正因佛性”成为南北朝佛性论的主题,本有与始有的争论[3],摄论师更是依本学派的立场而建构其学说。
1、第一义空、阿摩罗识与正因佛性
综合南北朝时代的佛性说,吉藏《大乘玄论》卷三列出正因佛性十一家,第七师“以阿梨耶识自性清净心,为正因佛性也”,第十一家是“以第一义空为正因佛性者,此是北地摩诃衍师所用”[4];前者是以心识为正因佛性,后者则是以“理”为正因佛性,即在境上成立佛性。《大乘四论玄义》卷七则说正因佛性有本三家、末十家之别:
地论师云:第八无没识为正因体,第十、摄论师云:第九无垢识为因体。故彼两师云:从凡至佛,同第九以自性清净心为正因佛性体。[5]
元晓《涅槃宗要》列出以真谛的佛性说为第六师,说:“阿摩罗识真如解性为佛性体,如经言:佛性者名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名为智慧。《宝性论》云:及彼真如性者,如《六根聚经》说,六根如是从无始来毕竟究竟诸法体故。”[6]
吕澂认为,《大乘玄论》第七师是后来的地论师和更后一些的摄论师所提出的,第十一师是北方涅槃师的共同看法。[7]结合吉藏、均正、元晓的记载,我们看出,《大乘玄论》第十一师则是摄论师的佛性说。这样,摄论师的正因佛性可以归纳为三种:一、自性清净心,二、第一义空、真如,三、第九无垢识、阿摩罗识、解性。[8]摄论师正是继承了真谛的佛性思想,以阿摩罗识为中心,这是综合了真谛的整个思想体系,而建构摄论学派的佛性说。
真谛在《佛性论》以二空所显真如为佛性,因此第一义空、真如为佛性,这是会通了《涅槃经》的说法。而真谛依真如无差别而说“阿摩罗识自性清净心”,约境智无差别而说无垢识、阿摩罗识、解性。因此,摄论学派的佛性思想具有“过程存在论”的特点,强调一种动态的过程存在;而且是依“解脱诠释学”“修”的立场,而诠释佛性的普遍性、必然性、实现性。但是,摄论师各依不同角度,于是便有种种的佛性说。
以第一义空、真如为佛性,这是属于以“理”为正因佛性,由客境建立佛性义。真谛以“二空所现真如”为应得因佛性,摄论师则依此而分开诠释。《中边分别论》说:“如道理依第一义相观此法空,是名第一义空。为得此菩萨修行空,是此法空为何修行?为至得二善:一、有为善,二、无为善,此空是名有为无为空。”[9]诸法性空是诸法存在的本然状态,不增不减,所以是“第一义空”。而且,在实践论与解脱论上,修习此法空,则能够得到二种善:一、有为善,二、无为善。摄论师是将“第一义空”作为超越相对的绝对真理,即是“非安立谛”,敦煌本《摄大乘论疏》卷七(S.2747)说:
本为对俗识立真如,俗既空无所对,真亦绝待第一义空。如见四微亦无所有唯空,即是真实性成无性性,即非安立谛,无于二谛、三性等也。[10]
建立真如本为遣除世俗虚妄心识,既然世俗谛无所有,真谛则无所立,于是真如即是“第一义空”,真实性变成“无性性”。所以,“第一义空”是超越于一切语言与思惟活动之外的无分别境界,因此是“无性性”、“非安立谛”,而且超越于二谛、三性等建构性的真理。
所以,以真如、第一义空为正因佛性,其涵义是相同的。真如是一种建构式的真理表达(安立谛),第一义空则是解构式的真理表达(非安立谛);从“真如”之超越性不落入经验范畴,此即是“第一义空”;因为在经验界之外,超越界唯一无二的。摄论师正是立足于超越界的解构式真理,而诠释佛性。慧恺《大乘唯识论序》说:
如法空者,所谓佛性清净之体,古今一定。故经云:佛性者,名为第一义空。所言空者,体无万相故;言其空无万相者,无有世间色等有为法,故无万相。非是同于无性法,以其真如法体。是故经云:去八解脱者,名不空空,是故不同无法空也。若如是观,是名解真如法空。[11]
“第一义空”依存在论,则是解构式的真理表达;而第一义空为佛性,则是解脱论意义上的建构式的表达。二者是不同的诠释角度。真如、第一义空为佛性,则具有普遍性、必然性,超越时空之限制,所以是“古今一定”。但是,佛性毕竟成佛根据,必须具有“可能性”,所以是“无性之性”、“不空空”。
以真如为佛性,这是真谛原有的思想体系。摄论师受到《涅槃经》的影响,则亦将“第一义空”立为佛性。同时,摄论师亦将阿摩罗识作为佛性,这是以“心”为佛性。《大乘四论玄义》引用摄论师说:
彼宗八识、七识,即有真如性故。翻《摄论》等昆仑三藏法师明言,真如性于八识烦恼中有,而不为烦恼所染,亦非智慧所净。自性清净故,非净非不净。体既无染,不须智慧所净,故名非净;非非净者,断除虚妄,体方显现,故曰非非净,即是自性清净心也。彼论三种佛性中,自性住佛,如从凡夫,乃至金心,所有净识,未离烦恼,于烦恼中住。若尔,岂非惑识中有真如性也。[12]
真谛以“真如无差别”诠释阿摩罗识自性清净心,而摄论师则引用《中边分别论》的偈颂加以解释[13],这是对瑜伽行派“心性本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存在论来说,“自性清净”与“空性”相应,这是一种无变异性、普遍性、永恒性的法界清净,所以是“非净非不净”。但是,依解脱论,则必须知见染净差别而显现清净性。而且,摄论师依“真如”的普遍性,继承《佛性论》如来藏三义的“隐覆藏”说,将阿摩罗识、自性清净心与“自性住佛性”结合起来,从而建构了自己的佛性思想。
所以,摄论师继承真谛以真如诠释佛性的传统,而且将第一义空、自性清净心、阿摩罗识、解性等都纳入佛性的思想体系。但是,摄论师依超越立场诠释佛性,而很少涉及到无漏种子等问题,这样便很自然地对阿摩罗识、解性进行“本觉式”的解读,从而导致摄论学派思想的发展。
2、三种佛性与十胜相
我们一直强调真谛的思想是一种“中间路线”,其根本立场在于瑜伽行派,最明显的体现是以三性为中心,这是其思想体系的根本。[14]真谛亦是依三性思想对大乘佛教进行其富有特色的诠释,但是后来的摄论师逐渐背离了其立场,而与“真常唯心”系合流,强调以佛性为中心,这是摄论学派中国化的核心体现。
《摄论》一向以三性为根本,从而建立“十胜相”,以显示大乘的优越性。如真谛译《摄论释》说:
由唯识道得入三性愿乐位;六波罗蜜虽是世法,能引出世法,能生唯识道故,说是入三性因;菩萨已入地,出世清净六波罗蜜,即是入三性果。[15]
这是依三性对“十胜相”进行分类,依止胜相、胜相、入胜相是“唯识道”,这是证入三性的“愿乐位”;入因果胜相是世间六波罗蜜,这是“入三性因”;“入因果修差别胜相”是出世间六度,这是“入三性果”;最后的五种胜相,即是入三性因果差别。
但是,敦煌本《摄大乘论抄》则依“二谛”与“佛性”概括《摄论》的中心,这与无著、世亲及真谛的原意都有很大的差别。《摄大乘论抄》说:
言二谛者,若论世谛,即以唯识为所诠宗旨;若说真谛,即以二无我真如为所诠宗旨。故下释云:一切法以识为相,以真如为体故。又云:知尘无所有是通达真,知唯有识是通达俗也。[16]
摄论师继承了真谛的唯识思想,主张识具有自我否定性,于是识似现为境,即是境无识有,这是“世俗谛”;另一方面,识与境是所缘、能缘平等,其自体是空、无性,因此识融没于真如、空(真实性)中,这就是“真谛”。
摄论师的最大特色在于以“佛性”诠释“十胜相”,这完全是以如来藏缘起来解读《摄论》。《摄大乘论抄》以第一、第二胜相为“自性住佛性”;中间的六种胜相是“引出佛性”,通过修行唯识观等,断除烦恼等,显出自性住佛性;最后的两种胜相是“至得果佛性”,即是自性住佛性通过引出佛性而显现。这样,“十胜相”即是三种佛性。但是,佛性毕竟是超越的存在,而《摄论》的“依止胜相”、“胜相”是以阿黎耶识、三性为诠释对象,这是虚妄唯识的层面,如何以佛性含摄虚妄唯识,成为摄论师的重要问题。《摄大乘论抄》说:
二、约性者,论圣人兴教意,正欲显理成行、行成得果故。初二胜相即自性住佛性。于中初胜相,若论心功能即是如实因缘,若据实是心真如。故下《释》云:此即此阿黎耶识界以解为性,此界有五义等也。亦名不空如来藏,《地经》亦明缘阿黎耶识作第一义谛观,即心真如也。何者?是染染依止观,此明心功能与十二因缘染法为依止,即如实因缘也。第二胜相中,若就相即是三性,是前因缘所生果;若据实三性本不有,即无三性,名空真如,亦名空如来藏。故下《论》云:如取不有,故三性成无性也。此空、不空二种真如,法相所摄,二实体无二故。[17]
摄论师亦是通过“真如”来诠释佛性,但是其重视超越层面,这与无著、世亲、真谛有根本的不同。《摄大乘论抄》作者认为,以阿黎耶识为依止,这是成立杂染诸法的“如实因缘”;而在真实、超越层面,是“心真如”或“真如心”,即是“解性”,这是“不空如来藏”。而且,依阿黎耶识而建立三性,这是因缘所生果;在真实层面,三性同一无性,即是三无笥,这是“空真如”、“空如来藏”。
《摄大乘论抄》深受地论学派的影响,其“心真如”与净影慧远的“真识心”有相似之处。但是亦有其独特思想。净影慧远以真识心为佛性,依分相门、摄相门诠释真识心与生灭的现象法之间不一不异的关系,而且从究竟意义上,生灭现象法是以真识心为体。[18]《摄大乘论抄》以真如诠释不空、空如来藏,继承了真谛的思想;真谛以“道前真如”为自性住佛性,摄论师则将此立场扩展至虚妄唯识,从而使诠释模式发生变化。我们强调,真谛依瑜伽行派的立场来融摄如来藏、佛性思想,是“从下往上”的诠释模式。但是,北地摄论师明显背离了真谛的立场,而以如来藏本身的立场而诠释佛性,于是变成“从上还下”的诠释模式。
二、本有与始有
南北朝佛性思想的主流是“众生有性”,其内部论争主要表现为“本有”与“始有”之争。
赖永海先生指出,本有说主张佛体理极,性自天然,一切众生,本自觉悟,不假造作,终必成佛,这是以理性和因性释佛性;始有说则认为清净佛果,从妙因生,众生觉性,待缘始起,破障开悟,当来作佛,这是约果立言。[19]受南北朝“本始之争”的影响,摄论学派的佛性思想亦出现“本有”与“始有”的不同诠释。
1、真性与本有
摄论学派以真如诠释佛性,真如具有普遍性、必然性、永恒性,故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摄论学派的佛性思想应该是属于“本有”论者。[20]从真谛的佛性思想来看,《佛性论》强调佛性不但在各类众生中无差别,在各个证悟阶位中无有差别,而且在任何时空之下,其体性亦无有变异。《佛性论》举出六种无变异,而且引用如来藏九喻,如强调法身佛性前后际无变异,《论》曰:
法身非本无今有,本有今无,虽行三世,非三世法。何以故?此是本有,非始今有,过三世法,故名常。[21]
法身、佛性是“本有”的无为法,不是本无今有、本有今无的生灭法,超越时空,所以是恒常的。而且《佛性论》以“金堕不净”比喻“如如”有三特性——性无变异、功德无穷、清净无二。因此,摄论学派的佛性是属于“本有”。
摄论师以真如为佛性,真如是超越的理体。吉藏曾以地论师“理非物造”谈本有[22],地论师南道派以法性、真如为依持,与摄论师的佛性相近。[23]所以,均正《大乘四论玄义》以地论师与摄论师的佛性都是属于“本有”,均正说:
本有藏识心性之体也,但客尘烦恼隐覆此心,不显不照。若除烦恼,本有之心显了照用,尔时名佛,不以成佛时方名佛性。正以本有藏心,今显成佛。其本性不改不失,故名常住佛性也。故彼云:息妄显真,正是《地》、《摄》等论所执也。[24]
真谛的佛性思想仍然是一种“中间路线”,真如并不是“本觉”。但是,北地摄论师受到地论学派的影响,对“解性”、“阿摩罗识”进行“本觉式”的理解,于是造成摄论、地论学派的佛性思想趋于相同。
佛性为众生所“本有”,即佛性本潜存于一切众生生命之中,不用外求。而众生之所以不能显现佛性,因为有种种染污的东西把佛性障蔽之故。若能将此等障蔽除去,则众生便可显现佛性,得觉悟而成佛。摄论师强调不以成佛果位为佛性,而是以因位的本有藏心为佛性,“藏心”即是说明佛性隐藏于烦恼中。所以,实现佛性的方式是“息妄显真”,摆脱烦恼而显现真性。摄论师强调了佛性的普遍性、内在性及实现问题,但是佛性的“显了照用”,明显与真谛的原意不同。真谛虽然以真如为佛性,但是真如作为存在之“理”,与众生的心性结合,才能成为觉悟主体;真谛突出了真如的普遍性、必然性,而其“内在性”明显不足。而中国佛性思想经过道生“性理不殊”,“理”具有体、性二义[25],从而将普遍性与内在性进行很好地结合。摄论师的佛性思想正是在真谛的基础上,以“本觉”、“理”进行诠释,从而促进本学派的中国化。
摄论师的佛性“本有”说,应该是比较普遍地说法,道基《摄大乘义章》卷四(大屋德城氏藏敦煌写本)说:
依他必从种子生因而生,真如本有,非生因生,故非依他。而彼真如藉缘而显,说有了因。《摄大乘》云:四德本来是有,不从种子生,从因作名故名种子。[26]
真如作为超越理体,非生灭法;而依他起的有为法必然是由种子而生。真如的显现必须由般若智的透视才能显现,所以般若智是一种“了因”。但是,真如以及常、乐、我、净四德本来是有,因为凭藉般若智之缘而显现,所以称为“种子”。
摄论师以佛性“本有”的普遍性与内在性,来证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是“全分有”。[27]灵润正是通过引用《涅槃经》作为说明众生皆有佛性的依据,同时他批评无性说是“不了义”,因为“二乘人说有佛性,虽有违小乘九部之教,以理当故即是实说,非是妄语。”[28]同时,由于《宝性论》及《佛性论》都提出“悉有佛性”三义,证明了法身的遍在性、无差别性、隐覆性,佛性的本性不改不失,所以一切众生是“全分有”佛性。
但是,在中国固有思想的语境下,中国佛教借鉴中国哲学“理”范畴的涵义,逐渐把法性、真如、理三个概念等同起来,不仅视“理”为真理,且以“理”为宇宙人生的本体,众生证悟的根本与目标,强调悟理以成就佛果。[29]摄论师亦受到中国佛学“理”的影响,以“理”的普遍性、超越性、内在性而证成佛性,道基《摄大乘论释序》说:
《摄大乘论》者,盖是希声大教,至理幽微,超众妙之门,闭邪论之轨,大士所作,其在兹乎。若夫实相宗极,言亡而虑断;真如体妙,道玄而理邈;壮哉法界,廓尔无为;信矣大方,超然域外。……三性殊旨,混为一心;六度虚宗,俱拪彼岸。蹑十地之龙级,淤三学之夷路。涅槃无处,运悲慧之两融;菩提圆极,齐真应之一揆。[30]
道基以老庄哲学的“道”、“理”来诠释实相、真如,强调其形而上的普遍性、超越时空。真谛是佛性以三性为体,亦以三无性为体;而道基则融“三性”而入一心,这是以佛性为中心而诠释三性思想,与《摄大乘论抄》相一致。
同时,亦有摄论师坚持将三性、三无性与佛性相结合,进行“解脱诠释学”的诠释。敦煌本《摄大乘论疏》卷七(S.2747)说:
所解脱无所有为无相性,能解心亦不得生,无相无生即得解脱果。了因即无分别正体智,此智为不生道;四如实智是对治道,正灭障也。应除是俗谛,二性可解,除灭者即为已灭。已灭惑即理显现,理显现即三无性。一切法悉本来无二相,故除生死、得法身,皆由唯识观成。[31]
摄论师以“理”为三无性,这是一切事物的本然性,显现“理”必须断惑,即通过四如实智对治惑障,而无分别智是“了因佛性”,这是证入“理”的真实主体。从存在论来说,分别性是解脱的对象,本无所有,是无相性;而能解脱的虚妄主体本来不生;无相无生即是真实性,三性同一无性,即是“理”。这样,存在论与实践论、解脱论得到结合,所以是一种“解脱诠释学”。虚妄主体的根本是“不觉”,而真实主体的根本是“觉”,在这种意义下,通过唯识观的修习,而产生无分别智,便能断除生死而证得法身。

总之,摄论师将真如、理等同起来,以诠释“本有”佛性的普遍性、内在性,依此而批评新译唯识的“无性”与“少分”。
2、亦本亦始与三种佛性
从真如本有可以说佛性“本有”,但是真谛的佛性思想是一种“解脱诠释学”,不仅是超越的存在,更包含实践论与解脱论。真谛提出三因佛性,应得因是人、法二空所显真如;加行因是指菩提心,由菩提心而行十波罗蜜等助道法;圆满因是指由加行而得果圆满。在“应得因”中又建构三种佛性——自性住佛性、引出性、至得性。所以,在真谛的佛性思想中,不但强调因与果之间的必然联系,亦注重因果转化的条件性,由三因佛性、三种佛性出发,应该是“亦本亦始”。[32]
真谛依三真如诠释三种佛性,智顗依正因、缘因、了因解释三种佛性,《法华文句》说:“道前真如即是正因;道中真如即为缘因,亦名了因;道后真如即是圆果。”[33]自性住佛性是正因佛性,引出性是缘因、了因佛性,而至得佛则是圆满果位。正因佛性是所觉悟的终极真理,亦是真如、法性、实相;了因佛性指观照终极真理的心能,即是般若智慧;缘因佛性则是般若以外的五度等其他修行。对于三种佛性的理解,摄论师存在分歧,《大乘四论玄义》说:
故彼云:自性住佛性,引出佛性,得果佛性也。此引出、得果两性,彼师解不同。一云:三性并是正因性。一云自性住是正因性,余二性非,何者?果与果果两性,是得果性;引出性,即是十二因缘所生观,知了因性;自性住是非因非果,佛性正因也。[34]
摄论师对三种佛性存在两种看法:一、三种佛性都是正因佛性,因为三种佛性都是以真如为体,真如是正因佛性,自然三者皆是正因,这是从体上而言;二、自性住佛性是正因佛性,天然本有,非因非果,而引出性是了因佛性,果、果果则是至得性,这是因果转化而言。
若以三种佛性皆是正因者,其佛性则是“本有”;而以自性住佛性为“本有”,而引出性为缘因、了因佛性,其佛性思想则为“亦本亦始”。二者都是从不同角度而言,并不存在矛盾。道基《摄大乘义章》卷四(大屋德城氏藏敦煌写本)说:
问曰:所以断惑非余识也?答曰:第一净识体是如如,真性本有,非始修智,不说断惑。阿梨耶识唯有净品闻熏种子,以是成就不能现行照理断结。[35]
真如是清净法存在的根据、体性,本有而非始有;而般若智是始有,依般若智才能断惑证真。但是在凡夫位,迷染阿黎耶识虽然有清净闻熏种子,但是不能依闻熏种子而直接断惑。闻熏种子是生起般若智之因,般若智是“正治”,而净种是对治因。所以,摄论师坚持“亦本亦始”,这是实践论与解脱论的需要,是“解脱诠释学”的体现。
灵润正是从“亦本亦始”的佛性说出发,对新译唯识“理性平等,行性差别”进行评破。玄奘继承印度瑜伽行派“法界无差别而种性差别”的矛盾结构,提出众生皆有“理佛性”,而一分有性众生则无“行佛性”,故不能成佛。灵润坚持有“理佛性”则必有“行佛性”,因为“行佛性”是“理佛性”的作用与功能。《宝性论》说:“若无佛性者,不得厌诸苦,不求涅槃乐,亦不欲不愿。”[36]佛性的作用有两种:一、厌离生死苦,二、乐求涅槃解脱。所以,理佛性、行佛性虽然各有特性,但是二者非一非异,理佛性由行佛性而显,行佛性由理佛性而立,二者不相舍离。[37]而且,摄论学派的三因佛性、三种佛性都是一体,所以有理佛性即有行佛性。灵润假设有人问难说:
问:若有理性即有行性,草木无情有理性故,应有行性。
答曰:草木无情无有理性。故《涅槃经》云:非佛性者谓墙壁瓦砾无情之物。[38]
因为真如作为“理佛性”,具有遍在性,如果有理佛性必有行佛性,也必须承认草木有行性,因为草木亦有“理佛性”。但是,灵润回答草木是无情,没有“理佛性”,这样便有违“真如遍满”义。灵润进一步回答说:
草木唯心量,心外一向无,故无有理性非是心外有,真如何所遍?又《摄论》云:由内外得成,是内有熏习。有熏习者则有行性,外无熏习故无行性。复次真如无内外,不离于内外,在内名佛性在外不名佛性。[39]
灵润主张“理佛性”是本有,而“行佛性”则始有。“内种”的心才有熏习作用,而草木无心,没有熏习种子,所以
没有“行佛性”。虽然真如理遍满内外,但是始有“行佛性”则唯有情才有,所以只有有心的众生才有佛性。
所以,摄论师依三种佛性说“亦本亦始”,并依此而批评新译唯识“理性平等,行性差别”。但是,其佛性思想仍局限于有情众生。吉藏则依“唯识理”和“修证理”而言理内、理外佛性,则向草木皆有佛性转化[40];天台宗湛然则提出“无情有性”,进行很好的推演与论证。
三、究竟一乘与真实胜乘
日僧最澄在《决权实论》一书中,列出一堆主张一乘的中国、新罗、日本的思想家,其中有真谛、灵润、法宝等。[41]真谛在不违背瑜伽行派的前提下,将“密意一乘”转化为“究竟一乘”。摄论师的一乘思想的理论基础亦是真如无差别,敦煌本《摄大乘论疏》卷七(S.2747)说:“见如来大小乘教虽显多种法门,皆为成就真如一味无差别之理,一即法界之法身也。”[42]大小乘是属于法门的差别,三乘圣者都证入无差别的真如理,即是法身、法界。敦煌本《摄大乘论疏》卷七(S.2747)又说:
明大乘通三乘中菩萨为大,又待小得大。一乘者无二,三乘唯是一故。无相待之乘,为真实胜乘也。无分别智以法界为根,体为知根,从知未知根生故,又名有根。有未知欲知根,从如实智生。又论缘因解性生亦名有根,能生后智及进后加行智故,亦名有根。有当体名有根,何以然?得此智故余智灭,智依此智故更生上地功德智慧,故是根也。[43]
摄论师主张“究竟一乘”,三乘与一乘没有差别,所以便没有二者的对待,所以称为“真实胜乘”。这是从“性”立场来说,真如理没有差别,即使是“密意一乘”亦有此主张。但是,在“修”立场,摄论师强调依法界而生无分别智,这是依法界为所缘缘而生,所以称为“根”。而且,在“发心住”,解性与闻熏习和合,便能为生起圣道的依止,所以“解性”亦是“根”。这样,功德智慧便能层层升进,最后终至圆满解脱。
所以,摄论师亦是继承真谛依“修”立场而主张“究竟一乘”,并且依智慧的升进作为根本。同时,北地摄论师受到地论学派的影响,依《胜鬘经》、《起信论》而建立“究竟一乘”。如敦煌本智凝《摄论章》卷一(S.2048)引用《胜鬘经》,说:
经言:法者说一乘道,法僧者是三乘众。此言一乘道者,三乘所依,人别法通,故名一乘。此偏就道谛为语。又云:说一乘道法,得究竟法身。于上更无一乘法事者。此明因得果灭道通论。[44]
智凝认为,三乘人都是依一乘道,法是相同的而人有差别。但是,从究竟意义上说,得究竟法身是相同的。
《摄大乘论抄》引用《起信论》“三大”来解释大乘的“大”:
言大者有三种:一、体大,即目前空、不空二种真如,平等不增减故也;二、相大,即真如体上具恒沙无漏性功德差别故,名相举一一德皆遍满法界故常故,故名大也;三、用大,即此真如在因有任持染净内熏等用,至果有起应、化二身无住处涅槃等用,举一一用皆遍法界故常故,所以名大。虽情见有废兴,用恒常也。[45]
体大是表示真如的平等无差别,真如常在动态的超越的活动中,所以其表现为具有无量无漏性功德,这样保证其能够发生一种力量使之在事上显现。于是,真如能够具有染净内熏的作用,而生起化身、应身乃至无住处涅槃。这些无漏功德及其作用,都是依真如体而遍在。
但是,《摄大乘论抄》不但以三种佛性解释“十胜相”,更以三种佛性解释“乘”:
乘者有三种:一、理乘,即初二胜相、自性住佛性;二、行乘,即中六胜相、引出佛性;三、果乘,即后二胜相、至德果佛性。故下《释论》明,乘有三义:一、性,二、随,三、德也。三世诸佛菩萨依乘,此法别如来地故名乘也。
摄论师对真谛的“乘”三义进行自己的诠释,完全与真谛不同。真谛是以三无性为“理乘”,以十波罗蜜为“行乘”,以“四德果”为“果乘”。真谛是依“修”的立场而诠释“究竟一乘”,而《摄大乘论抄》则依“性”的立场,以佛性为中心而进行诠释,二者立场明显不同。真谛的“究竟一乘”义并不违背瑜伽行派,而摄论师则完全是真常唯心的思想。
四、结 语
真谛在不违背瑜伽行派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提出“一性皆成”与“究竟一乘”,从而建构了摄论学派的佛性思想。真谛之后的摄论师,由于受到北方佛教的《十地经论》、《涅槃经》的影响,更加努力去重建与弘扬本学派的佛性思想。而且,逐渐偏离了瑜伽行派的立场,而融入当时中国佛教界的“主流”真常唯心思想。另一方面,唐初摄论师接触新译唯识的“五性各别”,便对其进行批判,高举“一性皆成”的旗帜,于是便出现唐初佛性论争的局面
摄论师继承真谛以真如诠释佛性的传统,而且将第一义空、自性清净心、阿摩罗识、解性等都纳入佛性的思想体系。而且摄论师逐渐背离了瑜伽行派的立场,而与“真常唯心”系合流,强调以佛性为中心,以“佛性”诠释“十胜相”,完全是以如来藏缘起来解读《摄论》,这是摄论学派中国化的核心体现。同时,摄论师将真如、理等同起来,以诠释“本有”佛性的普遍性、内在性,依此而批评新译唯识的“无性”与“少分”;依三种佛性说“亦本亦始”,并依此而批评新译唯识“理性平等,行性差别”。摄论师依佛性解释“究竟一乘”,完全是真常唯心的思想。
[1] 释恒清指出,新译之后,佛性说的争论已从南北朝、隋代诸师探讨佛性本质的问题,更牵涉到大小乘种姓决定不决定,以及大小乘权实,本有或新熏无漏种子等问题上,使当时的佛性论内容更加丰富。基本上唐代佛性争议是性宗和相宗彼此间之评破。玄奘唯识新义传译之后,引起两波对论。一为灵润反对无性说,高唱一性皆成宗义,神泰造论反驳,新罗义荣随之造论支持灵润。第二波法宝造《一乘佛性究竟论》阐扬一性说,慧沼则着《能显中边慧日论》反驳之。《佛性思想》,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版,第239-240页。
[2] 《法华秀句》卷中,《日本大藏经》第42卷,第68页。
[3] 赖永海指出,本有与始有的争论,其原委,实由对佛性义之解执不同所致。以因说佛性,佛性当然是本有;以果说佛性,佛性必须始有;于当果说晔性,则佛性亦有亦始;以非因非果之中道义说佛性,佛性则又成为非本非始。《中国佛性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9页。
[4] 《大乘玄论》卷三,《大正藏》第45卷,第35页下、36页上。
[5] 《大乘四论玄义》卷七,《卍续藏》第74册,第93页上。有关《大乘四论玄义》的研究,见伊藤隆寿《大乘四论玄义の构成と基本的立场》,《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2号,1972年;同氏《慧均〈大乘四论玄义〉について(二)》,《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0卷第2号,1972年。
[6] 《涅槃宗要》,《大正藏》第38卷,第249页中。
[7]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第121页。
[8] 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488页。Ming-Wood Liu ,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Buddha-nature Doctrine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16,1989 , pp.23.
[9] 《中边分别论》卷上,《大正藏》第31卷,第452页下-453页上。
[10] 《摄大乘论疏》卷七,《大正藏》第85卷,第994页中-下。《敦煌宝藏》第23册,第91页下。
[11] 《大乘唯识论序》,《大正藏》第31卷,第70页中-下。
[12] 《大乘四论玄义》卷七,《卍续藏》第74册,第88页下-89页上。
[13] 《中边分别论》卷上说:“不染非不染,非净非不净,心本清净故,烦恼客尘故。”《大正藏》第31卷,第453页上。
[14] 上田义文亦强调,《摄大乘论》异于《大乘起信论》之根本点是把三性说当作体系的根本。《阿梨耶识の原始的意味》,《佛教研究》2-1,1938年,第45页。
[15] 真谛译《摄大乘论释》卷一,《大正藏》第31卷,第155页中-下。
[16] 《摄大乘论抄》,《大正藏》第85卷,第1000页中。
[17] 《摄大乘论抄》,《大正藏》第85卷,第1000页中。
[18] 刘元齐《净影慧远〈大乘义章〉佛学思想研究》,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年第1版,第379页。
[19] 赖永海《中国佛性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99页。
[20] 赖永海《中国佛性论》,第102页。
[21] 《佛性论》卷四,《大正藏》第31卷,第811页中。
[22] 《大乘玄论》卷三,《大正藏》第45卷,第39页中。“理非物造”出自净影慧远《大乘起信论义疏》卷上之上,《大正藏》第44卷,第179页上。
[23] 地论师的南道、北道与摄论师各有同异,南道派以法性、真如为依持,与摄论师的出世转依位相同;而北道派以阿黎耶识为依持,与摄论师的虚妄唯识相同。
[24] 《大乘四论玄义》卷八,《卍续藏》第74册,第111页下-112页上。
[25]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89页。吴汝钧认为佛性具有广狭二义:从狭义上说,佛性为众生成佛的基础,这只限于众生的主体方面;从广义上说,则佛性为现象世界中所有存在事物的基础。在这两义中,以广义的佛性观较为后斯的中国佛教所重视。见《中国佛学的现代诠释》,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0-31页。
[26] 《摄大乘义章》卷四,《大正藏》第85卷,第1045页中。
[27] 灵润针对新译唯识的佛性思想提出批评,首先他全盘否定一分无性说,称它为凡小不了义执;其次,灵润批评新译所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小分,非全分一切”;最后,他评破“一分无情无佛性者,无有行性,若论理性则平等皆有”的说法。见释恒清《佛性思想》,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版,第242页。
[28] 《法华秀句》卷中,《日本大藏经》第42卷,第69页上。
[29]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783页。
[30] 《摄大乘论释序》,《大正藏》第31卷,第152页上-中。
[31] 《摄大乘论疏》卷七,《大正藏》第85卷,第996页上。
[32] 赖永海指出,本有说在谈论因与果的相互关系时,更注重二者间的必然联系;始有说则在严分二者的基础上,强调因果转化的条件性。见《中国佛性论》,第108页。
[33] 《妙法莲华经文句》卷第八上,《大正藏》第34卷,第110页下。
[34] 《大乘四论玄义》卷七,《卍续藏》第74册,第93页上。
[35] 《摄大乘义章》卷四,《大正藏》第85卷,第1036页下。
[36] 《究竟一乘宝性论》卷三,《大正藏》第31卷,第831页上。
[37] 释恒清《佛性思想》,第245页。
[38] 《法华秀句》卷中,《日本大藏经》第42卷,第74页上。
[39] 《法华秀句》卷中,《日本大藏经》第42卷,第74页上。
[40] 见杨惠南《吉藏》,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1版,第248-252页。
[41] 安藤俊雄、薗田香融《最澄》原文“《决权实论》”,东京岩波书店1974年第1版,第388页。
[42] 《摄大乘论疏》卷七,《大正藏》第85卷,第999页上;《敦煌宝藏》第23册,第98页下。
[43] 《摄大乘论疏》卷七,《大正藏》第85卷,第999页中;《敦煌宝藏》第23册,第99页上。
[44] 《摄论章》卷一,《大正藏》第85卷,第1025页下。
[45] 《摄大乘论抄》,《大正藏》第85卷,第1000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