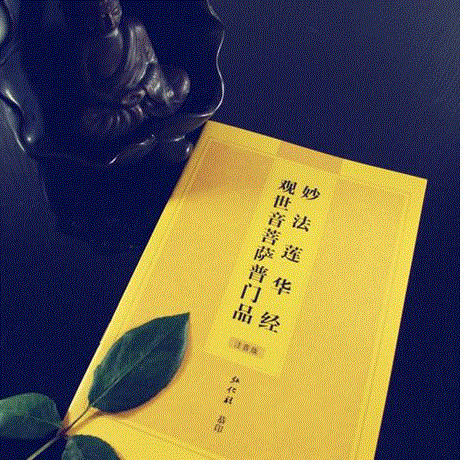达照法师:超越死亡 第三章 第二节 临终关怀之范围
发布时间:2024-08-12 03:00:32作者:普门品全文网第二节 临终关怀之范围
人生是个五味俱全的神秘盒,也是个丰富多彩的百宝箱。生活的色彩斑斓,心灵的波澜壮阔,直令愚者茫然无措,智者感动不已!死亡是人生的终结,蕴含了生活的所有信息,带走了生命的全部内容。因为学会了生活,才能学会死亡,所以临终关怀也就覆盖了对于整个生命的关怀,包括生活和死亡。
死亡,使许多人感到畏惧、讨厌,人们都觉得死亡是个不祥的代称,平时都不敢提到它,生怕说到死亡就会带来晦气。这种对于生命的无知,真的令人感到可笑而又可怜!大家都这样认为的事情,即使不是真理,也会习以为常,约定成俗了。因此,人们也厌弃与死亡相关的老人、病人、濒临死亡的人。而行将就木的临终者,在这样的氛围里挣扎,其痛苦和孤独的哀绝情绪,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人把佛教说成是死亡的宗教,那是因为佛教非常关注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死亡,佛教对于死亡的重视,一点儿也不亚于对生存的重视。也有人说佛法是人生的哲理,那是因为佛法把死亡与生活看成同样属于生命的体现。而当生与死都超脱了的人,再来看佛教和佛法,就会明白佛法的真实意趣却是在——不生不灭!
近年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使许多人开始关注死亡,无论是哲学思想、科学理论、文化学说、宗教见地,还是医学实践、人伦需求、社会稳定,都对死亡以及相关的老病死进行不同程度的关怀。死亡学的产生,护理团的成立,也都说明了人类不应该漠视死亡。而在这些临终关怀的领域里,其关怀的范围和深度,还是极其有限的,可以说并没有抓住生命内在的死亡真相。
佛教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对生与死进行了全面的透视,在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年代,在老子“吾之大患以吾有身”的时候,在西方“生死由上帝来安排”的那刻,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就作了全面的临终关怀,这不得不令人敬仰皈依!
从这里可以看出,临终关怀是人生的一项巨大工程,死亡和生存同样是神圣庄严的人生大事,对临终的关怀也就是对生命的珍爱,对生活的重视也就是对临终的关怀,而这项工程的实践范围,遍布了所有生命的每个角落,这是我们必须明白的“生死一如”。
一、关怀老病死
对于整体的临终关怀而言,表现得最为切近而急需的,那就是正面的临终关怀,因为正面的关怀就是直接针对死亡的挑战,这也是社会上所关注的临终关怀之范围。不过佛法中的关怀显得更有系统,更有思想理论和操作方法,其中包含了对于老人、病者、临终者的关怀。
1、老者
人生在世,众苦充满,八苦交煎,难以尽言!老,就是其中一种谁都不能避免的苦痛,佛经中称之为“老苦”,即衰老时身心所受的苦恼。如《中阿含》卷七〈分别圣谛经〉所说的:“老者,谓彼众生,头白齿落,盛壮日衰。身曲脚戾,体重气上,拄均而行。肌缩皮缓,皱如麻子。诸根毁熟,颜色丑恶。是名为老。”[1]体力之衰竭,生活之不便, 真是青少年强壮之时无法想象的悲哀啊!
《瑜伽师地论》卷六十一指出老有五种相:一、盛色衰退,二、气力衰退,三、诸根衰退,四、受用境界衰退,五、寿量衰退。老,就有这五种衰退,所以能生众多的痛苦。《大乘义章》卷三本亦说:“衰变名老,老时有苦,就时为目,名为老苦。”世间的无常,能令一切壮色不停衰变。《梵网经》说:“壮色不停,犹如奔马,今日虽存,明亦难保。”
因此,佛陀在最后的涅槃会上语重心长地说:“世间一切,皆是无常、败坏、不安之相。”没有人能够避免老死相催,也没有人不曾见过老死的无奈和哀苦。佛陀也告诉我们“老死是苦”的。
然而,对老者的关怀依旧是佛法中极为重要的一课,因为关怀老者就是临终关怀的预习。
佛陀是十分尊重老人的,有一天,佛陀出外游化,有一位八十岁的老翁来到僧团要求出家修行,根据留在寺庙里的佛弟子观察,此人八万大劫之内都没有种下善根,没有善根的人是不能出家学佛修行的,所以就被拒绝了。老人很伤感地流着眼泪回去了,在回家的路上,恰好遇到佛陀游化归来。佛陀问他为何如此伤心哭泣?老人诚恳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思。佛陀很同情这位老人,也很尊重他的选择,就亲自答应他,而度他出家修行。佛陀是珍爱真理的人,真理能够使任何人得到解脱,但要人们能够真正发起接受真理的诚心。
在《杂宝藏经》卷一记载了“弃老国”的故事,提倡“一切国土,还听养老。……其有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当加大罪。”佛教寺院也常常设有“安养堂”,又叫“安老”,就是指禅院中,老僧与隐居者所安住的寮舍。于此安住的人,如果年龄到了七八十岁,则可免一切勤行作务而供给粥饭。专门让年老而身体衰弱的僧人所住之处,也称为安老。另外,年龄虽老而能发道心,于僧堂中修行者,亦称为安老。这是教团中对于老人的特别关怀。
从方法上看,对于老者的关怀,一般包括这几个方面:
第一,年老体衰行动不便,所以老年比丘可以不参加体力劳作和集体共修方面的事务,使之安养年迈之躯体。对于生活起居不便的老人,还要安排年青人为之伺候,一般均由沙弥或新受戒的比丘来担任,称为侍者。对于世俗中的老人,亦应极力帮忙关怀。子孙后代应该注重孝顺赡养自他的老人,正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最佳写照。
第二,在精神上给予充分的尊重,生命的尊严就在死亡面前也不会逊色,帮助老人们消除过去生活的阴影,创造一个温馨、祥和、平静,而又充满尊严的氛围,打消他们因为“老态龙钟”而产生的自卑心和恐惧感。
第三,有些老年人容易脾气暴躁,抱怨亲人和社会,有时候很难听得进后辈的善言慰劝,这就需要寻访他们能够信任的人来开导他,或者恭请有智慧的长者来关怀其身心的健康和安稳。这样或许能够使其对生命产生新的认识,体悟获得新生的感觉,非常珍贵!
第四,最好能够在老年的时候,就提醒他们死亡的真相和有生必有死的事实,对于死亡的过程以及心灵的转换,都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和坦然的准备,这样就可以在迈向死亡的路上,有了明确的目标,具备美好的向往和究竟的归宿,这对于老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安慰了。孝子贤孙,不可不知!
第五,对于很多老人来说,最好的关怀就是静静地聆听他们唠叨,可以倾听他们数十年的风雨沧桑,可以静听他们的悔恨怨言和得意笑声。但要在聆听的时候,怀着无比的崇敬与爱戴,尽量让他们的思路在无形当中转入洒脱的境界。
总之,知识分子类的老人,需要的是活泼的赞美和尊重,一般老百姓的老人,需要的是真诚的谅解和鼓励。如果能够尽心尽力的关怀老人,那么这位老人的临终也将会得到殊胜庄严的好相,死亡也会是一种温馨的礼物了。
祝愿普天下的老人,都能够珍惜这段美好的死亡前奏曲!
2、病痛
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由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组成的身体,只要稍不调和,就会使身体感觉不适,产生病苦之相。比如身体苦重,坚结疼痛,枯痹痿瘠,属地大之病相;全身膨肿,肤肉浮满,属水大之病相;全身烘热,骨节酸楚,呼吸乏力,属火大之病相;心神恍惚,懊闷忘失,属风大之病相。这就是四大病相。
佛经中说四大不调就会有四百四病,如《佛医经》说: “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起四百四病。”[2]如果此等诸病辗转相钻,四百四病同时俱作,其人必会极寒、极热、极饥、极饱、极饮、极渴,时节失所,卧起无常。所以,病苦亦是人生之一大悲哀,无能幸免啊!
《摩诃僧祇律》卷十叙述了医治四百四病之方法:“病者有四百四病:风病有百一,火病有百一,水病有百一,杂病有百一。若风病者,当用油脂治;热病者当用酥治;水病者,当用蜜治;杂病者,当尽用上三种药治。”[3]
《瑜伽师地论》卷六十一说病苦有五相:一、身性变坏,二、忧苦增长多倍,三、于可意境不喜受用,四、非其所欲之不可意境而强受用,五、能令命根速离坏。可见病痛会使人产生反常的心理,甚至失去理智,心力憔悴,形容枯槁,甚可哀怜。
虽然对于病苦者来说,如果能够用药物来调治的,只要用现代高科技的医学来解决问题就行了。但是,疾病的痛苦毕竟会影响到心灵的感受,而内心的痛苦和绝望,也正是人们必须解决的关键所在。所以《北本大般涅槃经》卷十二亦有身病与心病之分,身病则有因水、因风、因热引起之病及杂病等四种;心病则有踊跃、恐怖、忧愁、愚痴等四种。佛经中还常说“八万四千病”,就是指八万四千烦恼。这是以病譬喻烦恼。凡夫之人烦恼无穷,难以计量。佛所说法乃为对治众生之诸病,故有八万四千法门。所谓: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毕竟来说,心病还需心药医。
同“老”一样,病也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所以佛教的正面临终关怀必定要从老病开始。对待严重的疾病,以及患了绝症的病人,也必须展开全面细致的殷切关怀。
佛法中对于病人的关怀,亦是慈悲而广大的。经典记载,佛陀曾经帮助一位眼睛看不见的比丘穿针和缝衣服,也曾为一个重病的弟子擦洗身体,帮他打扫卫生和喂其服药。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事,却透露出佛陀的完美人格,爱心和慈悲,以及佛陀一贯主张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平等观。
佛教的戒律是每个佛弟子必须严肃遵守的,但是佛陀制定戒律的根本目的在于“令僧安住”和“令正法久住”,也就是为了让弟子们能够安心地实践智慧的人生。所以,每一条戒律都有“开缘”的规定,开缘就是说在特殊的情况下,某些行为是不受该戒律条文之约束的。其中就有许多律文中注明了“除病”,说明生病的人是不受该条戒律所限制的。
就象对待老人一样对待病者,如上文所说,同样最重要的还是尊严和真诚的爱心!在尊严和真诚的感召下,病痛也会相应的减轻,如同做好了死亡的充分准备,在生与死之间留下生命的轨迹,会使人感到死亡更加接近生活。如果战胜了病痛的畏惧和恐慌,死亡就只是水到渠成的生命经历而已,就能以对待生活的态度来审视死亡,而无需逃避了。因此,对病痛的关怀也就成为临终关怀的神圣使命!
3、临终
临终就是指一期生命即将终结之时,即寿、暖、识三法将舍离之际,四大分离,水火交煎,如果平时没有刻苦修习认真训练,反而贪恋生活讲究享受的人,其间所经历之苦楚疼痛,犹如乌龟剥壳、热锅蚂蚁一般不堪忍受!即使没有肉体上的极大痛苦,也会有精神上的绝望、恐惧、无奈之悲哀!古颂云:“父母恩深终有别,夫妻义重也分离。人情似鸟同林宿,大限来时各自飞。”[4]即使豁达的人没有严重的痛苦和悲哀,也会是无能为力的“渺渺茫茫,不知何往?”
生不知从何所来,死不知去何所至,岂非人生之狭隘?岂非现实之悲哀?
佛法的临终关怀不但要令人微笑着面对死亡,而且还要阐明死亡之后的去向,甚至引导临终者当下觉悟真理,走向解脱自在的净土,一览生命中寂静光明的庄严美景!临终关怀的思想理论和操作方法,也是极为丰富圆满的。
如古印度之祇洹精舍设有“无常院”,系安置僧众中之重病者,使他们于面临死亡之时,能够放下对房舍、衣钵、道具等等物质的贪著,从而自在洒脱地走过死亡的关口,投向另一期生命的光明乐园。堂内一般都是供奉阿弥陀佛立像,其左手下垂,执五彩幡,临终者握幡之一端,表示随佛往生之意。后世之延寿堂、重病阁等,即采用无常院之范例。
对于临终者的开示,消除其心中之疑虑,令其身心愉悦;领导临终者念佛持咒或诵经,清净梵音使其心情明朗,解决其恐惧惊惶的心里障碍,而以积极平静的态度面对死亡。
重要的是为临终者解说佛法义理,使其明白人死并不是如灯灭一样什么都没有了,也不是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而是随着一生的善恶行为之力量,在六道中沉浮不定。更重要的是,轮回六道并不是生命的全部,而是一种迷惑的误会,消除生命中思想见地的迷惑,便可以当下解脱,冲出三界火宅、消除六道苦轮,到达常乐我净的微妙世界,那才是我们的究竟归宿。并且可以通过适合于临终者的方法,如临终助念等,帮助其获得这种胜妙的结果,才是真正值得赞叹的终极关怀。
二、觉醒成年人
佛陀告诉我们说:死亡随时都会降临,不要等待老病相催的时候才开始关注它,应该从此时此地就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死问题。是啊!人命在呼吸间,谁能保证自己明天或者下个月,死亡就不会降临呢?
现代人特别流行“自助”,自助餐、自助商场等等,这说明人们正在追求一种自由洒脱和独立自主的生活。我们在讨论临终关怀的时候,在佛法中,也同样表明了死亡也是可以“自助”的,而且也是比正面关怀的“他助”更为自由洒脱,所以我们这里就称其为“临终的自我关怀”。
但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依赖性,却大大地影响了自我关怀的质量和数量。佛法修学的重要目标就是了脱生死之苦,而于生死自在,亦即训练自我的临终关怀。通常,佛教徒也是以一个人的临终是否预知时至、洒脱自在,来判断其修行的功德是否成就。
有人说:伟人能够征服别人,却不能征服自己;圣人是征服自己,而感化别人。可见想征服自己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感化别人那就更难了。自我关怀就是要在临终之前能够征服自己,而反向关怀却要以自己的死亡来感化他人!
1、关怀自我
临终自我关怀的范围又如何呢?
首先,表现在临终的时候,能够自己作主,死生来去自由自在。对待自己的肉体和心灵之衰变,都没有任何挂碍,犹如“生故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不但明白了生何所来、死何所去,而且把握了自己的生命罗盘,任无常之风吹拂飘逝,此心也只有宁静洒脱和明亮。
其次,体现在死亡的形式上,可以坐脱立亡,可以安祥而逝,三昧火的自焚、化虹光而去、灭尽定涅槃,都是自我关怀的榜样。知道了自己要去的方向,明白了如何去的方法,就象拿起行囊离开旅店一样的平常,回归故乡一样的大方,死亡原来就是一台戏的曲终,另一台戏的登场,肉体的损坏,也只是换了一套戏装。
能够自我关怀的人,无论在形而上的精神世界里,还是在形而下的物质现象中,都能够坦然应付游刃有余,这是什么力量而导致的呢?
2、觉醒自我
成年人要懂得觉醒自我,所谓成年人,就是自己能够独立思考,并且懂得追求人生之完美幸福的人。这比起临终的正面关怀只是关怀老者、病人、临终者的范围要更加宽大,但这主要是由自己来觉悟、来关怀的。
当一个懂事的成年人,觉察到生命的意义时,他一定会在生与死之间思考许多问题,并且努力去探索生死的真相。佛法就要从这里开始指导和关怀,关怀其生死的迷惑、唤醒其生命的觉醒。
在佛教史上,得到这类关怀的人,真的是多不胜举。他们都是从成年懂事的时候开始思考,从接触到佛法的时候就开始觉醒,开始实践与生死赛跑的健康运动,打败了死亡的威胁,而最终获得生死自如的巨大胜利!
因此,当你读到这里时,无论你觉得死亡离你还有多远,你都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决心战胜这生死的迷阵,突出死亡的重围,看清死亡背后的真相,回到如实的生命乐园。
是时候了,你可以追求学习的成绩,可以追求工作的业绩,可以追求生活美好的结果,但是我告诉你,这一期生命的结果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这是事实,并非恐吓。
三、训练少年郎
大乘佛法真的是微妙无比的生命瑰宝啊!其“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伟大思想,完全来自于对生命的彻底觉悟。其“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洹。”的铮铮誓言,完全出自于真诚勇敢的肺腑心声。
哪怕到了死亡的那刻,修习大乘佛法的行者,依然谆谆善诱,不忘众生之苦,而反过来关怀身边的有缘众生,这是佛法中临终关怀的又一光明熀耀之处,也是生命庄严神圣的又一亮点。
佛陀就是这样的绝妙榜样,他老人家在临欲入灭之际,于一期生命的最后一昼夜,还宣说了生命真相常、乐、我、净的《大般涅槃经》,情感之深,意蕴之高,慈悲之远,智慧之广,真是人类福音,千古绝唱。类似佛陀的临终反向关怀,在大乘佛教史上比比皆是,特别是中国的历代祖师大德,几乎都能够在谈笑风生中走向圆满寂静,在死亡前仍然说法论道。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然而,这种反向关怀的培养,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获得的,也不是学了些许的理论概念就能达到的,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安祥,是一种生命内在的巨大力量,是佛法的终极目标之所在。因此,临终的反向关怀就需要从少年开始培养,其范围当然又比前面两种关怀更加广阔了。
1、关怀少年
或许你会觉得很奇怪,明明是说死亡的关怀,怎么又变成少年的关怀了?其实,在佛法里面的生活与死亡是密不可分的,佛陀曾经告诫弟子们说:“人命在呼吸间。”无论是少年、青年、壮年,还是中年、老年,随时都会面临死亡的威胁,所以随时准备死亡,随时透视死亡的真相,也是佛法指导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再说,这里要讲的是临终的反向关怀,那就让临终者反向关怀生活者,也就是让表面上看去很痛苦的人来帮助并不是很痛苦的人,这是生命中一种至高无上的尊严,许多佛弟子在临终的时候,都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也显示了唯有佛法才把生命的内在尊严全部挖掘出来,全部利用起来了。
关怀他人是一件好事,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特别是在贫穷困苦的时候,还能够欢喜踊跃地帮助他人,那就更是难能可贵了。人世间原本就有这样的真情,生命中原本也有这样的喜悦,佛法只是通过对宇宙人生的透视之后,发现了这种庄严,并且把它介绍出来,让一切佛弟子信受奉行,共同建构人间净土而已。
有人说:小时候学的东西是石头上刻的。少年所学的知识和接受的观念,是可以影响一生的,有些重要的人生观甚至就是到了临死的时候,还会记得清清楚楚。因此,在少年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关怀他人的良好习惯。
关怀青少年的成长,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青少年才是未来世界的主人啊!佛陀对于少年弟子也是关怀备至的,有一次小沙弥罗睺罗没有地方睡觉,躲在洗手间过夜,夜里差点儿被毒蛇所伤,佛陀知道后就赶紧把他叫到身边,进行了悉心的安慰,并因此规定沙弥要在比丘众中生活。后来罗睺罗证得密行第一的阿罗汉,帮助无数众生安祥地渡过生死苦海!
佛法中关怀少年的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告诉他们死亡必定会到来,所谓“莫待老来方学道,孤坟多是少年人!”使其从小就对死亡有个正确的认识。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明白了死亡的真相,那么在生活中就会更加珍惜生存的快乐,也就生活得更有骨气,生存的力量将得到比较完美的发挥,而且这种力量是取之不竭,受用无尽的。
2、训练少年
死亡给少年人的打击是至深的,每个人从小就会害怕死亡,再加上大人们的渲染,在幼小的心灵世界里就开始畏惧死亡,致使许多人到了临死的时候,还对死亡毫无认识、毫无准备,甚至毫无能力去面对,这是人类的悲哀。我们必须正视死亡给人类带来的种种作用,必须正视死亡的真相。
一个人到了临终的时刻,仍能坦然地关怀并未面临死亡的人,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完全可以通过训练来获得的。当一个人从小就喜欢关怀他人,哪怕是遇到了生死的威胁,也能置生死于度外,而把生命的庄严和力量奉献给他人,他就能够在死亡面前毫无畏惧地反向关怀!
当然,反向关怀的训练也就遍满了整个人生,随时意识到死亡的到来,随时准备为他人付出,随时感受生死的自在,这是何等福德何等超然啊!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佛陀就对于青少年进行了认真的关怀和培训,并且以戒律的形式流传下来。根据律典记载,七岁至十三岁的出家男子称为“驱乌沙弥”,意思是能够帮看谷场而驱赶麻雀飞鸟来盗吃谷子。七岁的孩童还没有别的工作能力,就可以接受僧团的生活,并以驱乌来训练其生活能力,同时也是训练他们关怀集体的观念,和关怀他人的品格。
其实,临终反向关怀的另一个秘密,那就是恭敬尊重临终者,特意恳求临终者为我们解说人生哲理,让他们来关心我们活着的人,使他们感到生命的无限价值,从而令其安住在愉悦祥和的心态中,安然地迈上死亡的征途!
由上可见,佛教临终关怀的范围,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对老人、病人、濒临死亡的人、成年人、青少年等整个人生的关怀,可以说就是对生命的全面关怀!所以,在了解甚至是接受佛教的临终关怀之后,也就会更深程度地了解生命的内涵,在茫茫生死海中,把握了生命宝舟的方向盘,驶向光明洁净的彼岸。同时,也引导他人进行自由洒脱的生命之旅。
--------------------------------------------------------------------------------
[1] 见《大正藏》卷一,第467页下。
[2] 见《大正藏》卷十七,第737页上。
[3] 见《大正藏》卷二十二,第316页下。
[4] 见《大正藏》卷四十七,第286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