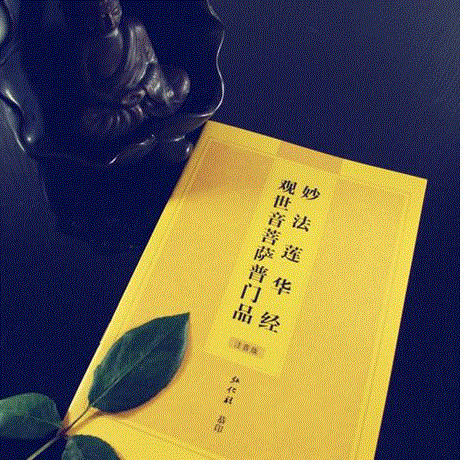谈锡永居士:四重缘起深般若 第四章 如来藏 3 龙树说法界
发布时间:2024-07-28 03:00:52作者:普门品全文网3 龙树说法界
龙树有一篇《法界赞》,在汉传佛教中少受重视,宋代施护的翻译,译得十分糟糕,满篇堆砌模棱两可的陈腔滥调,那应不是施护的错译,而是笔受的人根本不去理解颂意,只拿着译师译出来的名相来自由发挥,那便等如是他自己的创作,龙树的颂义,半点也没有传达出来。为此,笔者已将之重译,作为本章附录,不敢说丝毫无误,但却敢保证不失龙树的颂义。下来所引,即依拙译。
(附记:弟子邵颂雄告知笔者,龙树的《法界赞》有异译,即唐代传密法入汉土的不空三藏所译之《百千颂大集经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此译大部份内容同《法界赞》,唯其后多三十余颂说密法修习。由此或可推知,《法界赞》曾被结集入《大集经》内。不空译较施护译远为严谨。此外,多出来的三十余颂,其实即是行人观修《法界赞》的仪轨,依着仪轨生起坛城本尊,复加入圆满法的修习,如是依《法界赞》作抉择,复于观修时生起决定,是即为这些赞颂的内容。)
这篇赞颂,在藏传佛教中却深受重视,主张“他空大中观”的觉囊派,将它当成是根本论典,认为“他空”即是龙树的见地。格鲁派否定“他空”,视之为邪见,当然不认为《法界赞》说的是他空见,至于宁玛派,则认为龙树在这篇赞颂虽主要说至相碍缘起,未细说如何离碍始为究竟,但这仅是道次第的问题,不能由此证明龙树唯说“他空”,因为其实他提到离碍。
在这里,我们且依《法界赞》的说法来说法界,则可知“如来藏藏识”、“如来藏”、“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等名言差别——很可怜,这些分明是名言分别,如今却要落于名言分别边际,来澄清那些唯藉名言而横加于如来藏上的歪曲与垢障。我们生活的,真是一个名言分别的世界。
在《法界赞》中,一开头便说,三恶趣有情都住于法界,所以他都对这法界赞礼。
在龙树时代,这是一个崭新的概念,那就超越许多外道的层次。他们建立一个令人向往的世界,吸引信众,这个圣界绝对不同凡间。然而,原来我们这个世界器世界就在法界之内,所以我们实无所往,亦实无另有一个涅槃的住处。
那么,轮回界跟涅槃界又有甚么分别呢?
本质没有分别,都只是这个法身,但是境界却有分别,清净时名为涅槃,不净时名为轮回。所以在第2颂中,龙树立刻就指出[注15]——
以成一切轮理因 由道次第得清净
所谓清净即涅槃 此亦恰恰为法身
一切轮回因(一切不净)都可以由修学道次第而得清净,当清净时即名涅槃,此清净境即名法身。
他用牛乳与酥酪来比喻。酥酪混和于牛乳中时,只见牛乳不见酥酪,但当牛乳清净时,酥酪自然显现,这即如法身混和于烦恼中,只见烦恼缠而不见法身;只见烦恼有情的识境而不见法身此智境,是故唯于一切烦恼皆圆满清净时,法界、法身才得离障碍而显现。
对于这些障碍,他又作譬喻说:将酥油灯放在瓶子里面,那瓶子就完全障碍了酥油灯的光。假如我们在瓶壁上钻孔,从那里钻,光就自然从那里射出来,这是法尔、这是本然。这即是说,能离障碍,法身就自然显现,此时更无须造作。——要造作的,只是如何去钻穿瓶壁,这便即是道上之所为、道上的修学。
当于无学道上、佛的因地无间道中,行者于修证“金刚喻定”时,有如完全打碎这障碍酥油灯光的瓶,这时候,就周遍一切界而见法身。是故颂言——
无间金刚喻定中 即能除去瓶相碍
刹那光明炽盛燃 周遍一切界耀显
这便是由相碍缘起来说法身了。
因此,并不是杂染依于清净心识,也不是阿赖耶与如来藏相对,而是本初清净的法身受到障碍,这些障碍,在我们,即是所谓贪、嗔、痴等烦恼。
这些烦恼虽然亦无自性,但是却能起障碍的功能。所以龙树便以芭蕉作喻——
是故喻此器世间 恰如芭蕉空无实
然而其果却有实 食时口舌能触及
我们若能除去烦恼的障碍,便可以见“佛种姓”了,这便即是如来藏。因此接着便有一偈颂说——
如是轮理亦无实 但若除去烦恼壳
其中见佛种姓果 有情普尝甘露味
除去烦恼壳而见佛种姓(喻如壳中的果实),而且是“有情普尝甘露味”,这显然便即是说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而如来藏则受烦恼所缠,这便是龙树时代对如来藏的表达方式。
这也是我们于上来所说的,法身唯藉烦恼缠而显现。这个法身,从本性清净这点来说,可以说等同如来藏;但若从修证的角度来说,则如来藏便是成就法身时的证智境界(这境界亦即本性清净的境界)。
所以,龙树并没有将烦恼缠与法身截然分之而为二,它们可比喻为牛乳,只是智者却知道牛乳中其实有酥酪,因此二者其实非一非异。
由是法身便不是一个可以离器世间而独立自存的本体 (法界不是,如来藏当然更加不是)。所以龙树说——
法界不可说为自 既非是男亦非女
有情超越思议法 如何能说为自我
由烦恼缠而显现出来的情器世界,有男女等种种分别,但这一切分别其实只是名言。情器所依的法界,如何能说它是男是女,因为它根本“不可说为自”,连自性都没有,焉能落于种种分别的边际。所以落于分别的一切法,都是“思议法”(分别即是思议)。超越思议,即一切分别都泯灭,由是有情即现证“无我”,因为“我,即由分别而成立。
不但自我,一切法亦无自我。因为所谓自我,其实只是将一切法归于烦恼缠,这时候成立的便是识境。在识境中,一切法都说为有自我,但当将一切法归于法身时,它们便只是法界的自显现,法界既不能说为自,一切法自然也就没有自我,这便即是智境,亦可说之为如来藏。
龙树因此用印度的一种鹳鸟来作譬喻。这种鹳鸟于饮牛乳时,可以滤去乳中的水份,只饮乳份。这就即如行者观修,对境虽然是识境,可是行者却能现证受识境覆藏的智境。龙树的颂说——
此如水乳相混和 置于同一器皿内
鹳唯饮乳不饮水 于转依因即此喻
烦恼所缠本觉智 于一身中同得见
瑜伽行者唯取智 而留无明于其外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譬喻。由这个譬喻,就明白为甚么在相碍缘起中即可触证真如。对观修的人来说,识境虽然与智境相碍(无明与智相碍),但观修的人却可以取智而不取识,一如鹳鸟的取乳不取水。所以并非真的有一个“烦恼壳”要敲碎,然后才能现见如来藏、才能现见法身、才能现见法界。智境藉识境而成显现,行者并非须要排除这些显现(而且一排除便错,有如西谚所云:倒污水的同时,也倒掉盘中的孩子),恰恰相反,行者正须凭藉着这些显现,然后才能现证识境中含藏着的智境。
此即如龙树颂云——
佛种涅槃净与常 皆依法界而为基
未熟归之为二我 瑜伽行者住无二
佛种(如来藏)、涅槃、清净、恒常,都是法界的智境,因此说它们“皆依法界而为基”,这些智境不显现,但藉识境而成显现,由是未成熟的有情众,便执持识境而成立“人我”、“法我”,唯瑜伽行者则能于识境中住入智境,由是无此“二我”——也即是住入法身常、乐、我、净的境界。
在修学的层次上龙树以月为喻,概括地前至初地、初地至十地以前、十地至无间道,三个层次的修学。这比喻,上来已约略提过,现在则可说得较详细一些。
这里一共有三首偈颂。初颂云——
恰如天际苍黄月 赤裸见于十四夜
于彼发心趋道者 法身亦得赤裸见
这里说的,是初地以前,包括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上的行人。他们不能见到十五夜的满月,但是却能见到十四夜赤裸的月。所谓赤裸,即喻如脱离识境相碍的智境。然而其时实未离相碍,只是透过相碍而见,因此龙树便用“苍黄”来形容这时所见的月相(智境相)。
这时的境界,也可以说,有如钻穿藏着酥油灯的瓶壁,只穿一孔,行者乍见灯光。
次颂云——
恰如新月于天际 见其增长渐增长
于彼已登地位者 得见法身渐增长
这里说的,是见道初地至修道十地的修学。这一阶段,法身如由上弦月而至满月,渐见增长。当然,此际并非真的是法身增长,只是因为行者渐离障碍,由是便如法身渐见增长。关于这些,我们于上来亦已说过,修道上九个地位的菩萨修学,其实都可概括为修证离碍。在弥勒瑜伽行,即是观修胜义无自性性。
末颂云——
恰如十五朦胧夜 月已圆满无有缺
于彼已登极地者 法身圆满光澄澈
这里说的,是十地至无间道上行人的修学。因为尚未成佛,所以龙树便用“朦胧夜”来形容修学的背景。行者已现证满月,即已现证圆满法身。法身虽然光明,但是却仍未能周遍(所以朦胧),此即尚未能究竟现证大平等性。
龙树于《法界赞》中之所说次第,即到此为止。整体而言,无非都是于相碍缘起中修证离相碍。是故龙树亦有概括性的一颂——
于心究竟清净时 轮回笼破无局限
于彼妙莲花座上 相当地位彼承担
无局限,当然便即是离相碍。由离碍程度,即决定行者的地位。及至究竟离碍,则自然周遍一切界。此即如上来曾引述过的偈颂说——
无间金刚喻定中 即能除去瓶相碍
刹那光明炽盛燃 周遍一切界耀显
但我们却须知道,所谓光明炽盛,所谓周遍一切界,都无非是行者所现证的智境,这现证可名为智觉,与凡夫的识觉互成相碍。可是,假如局限于一器世间中来说,智觉的所缘境跟识觉的所缘境便实无有分别,因为分别不在于所缘境,而在于智与识。因此释迦成佛之后在我们这个世间,我们之所见便亦即是他之所见,只不过我们是执着二取与名言来看待世间,而释迦则离二取名言、见一切法实相。
周遍法界有无量无边、过于恒河沙数的器世间,每一个世间都充满生机,这些生机,依有情来说即是大乐,依法身来说便是大悲;每一个世间都有它们自己的烦恼,依法界来说,一切不同形态、不同建立的烦恼,无非都只是法身的自显现,因为智境须藉识境而显现、法身须藉烦恼缠而显现、自性清净心须藉阿赖耶识而显现、如来藏须藉阿赖耶而显现、法界须藉烦恼而显现。
这一切,龙树喻譬如水,于夏日中说水暖、于冬日中说水冷,而其水则同一,所以同一法界,佛可见其清净,而我们凡夫则见其烦恼。他说——
此可譬如夏日水 是可说之为温暖
此水若然于冬日 则可说其为寒冷
被诱入于烦恼网 由是得名为有情
于中能离烦恼境 是即尊称为佛陀
因此一切器世间不离法界、一切有情不离法身;法界周遍一切器世间、法身亦周遍一切有情世间。亦即——法身唯藉有情而自显现;法界唯藉器世间而自显现。
这就即是龙树所说的中道。
对于龙树的中道,如果光从“胜义空、世俗有”去了解,或说“无自性的缘起与缘起的空性相成”,无非都是名言,实非龙树的意旨。
龙树在《法界赞》中是这样说中道的——
以兔角喻牛角喻 此为如来所现证
是故于彼一切法 除中道外无所有
这即是说,唯能由中道成立一切法。而此中道,则可由兔角喻与牛角喻而现证。[注16]
我们且看看这两个喻。于兔角喻,颂言——
兔头上角为譬喻 除妄想外无所有
见一切法皆如是 唯妄想而非为有
这即是说识境无所有。因为识觉即是妄想(虚妄分别),由妄想所成为有的,唯是识境,对识觉来说,这识境可以说为有(虚妄分别有),但其实所谓“有”者,无非只是妄想,有如妄想兔头上有角。(在实际观修上,宁玛派又将“兔角喻”建立为非识境,此次第较深,在此不拟述说。)
于牛角喻,有二颂言——
非由实有极微成 是故牛角亦不见
以极微既无所有 极微成者焉成有
以其由缘起而生 以其由缘起而灭
故无一法可为有 童蒙妄想焉成有
这里说的是智境,智境亦无所有。智境由智觉而成,行者于初地后即能起智觉,但若对智境执之为实境,那就有如执牛头上角为实有。一切法缘生缘灭,非由极微所成,所以观修的智境实亦缘生缘灭,行人必须于智境中观察重重缘起,才能现证无一法可以为有。
龙树说,这二者即是释迎的现证,由前者知妄想为识境,证人我空;由后者知无所有为智境,证法我空,由是他才转*轮说缘起法。
颂中末后一句,指落于智境的人为“童蒙”、落于识境的人是“妄想”,但童蒙之想其实亦可说为妄想,因为行者若一旦执持智境,例如初地菩萨执持真如,则智境实亦变成识境,因为智境唯藉识境而显现,凡有所执,无非执其显现,这显现便即是识境。
所以龙树的中道,实在是识境与智境相成(双运)。透过识境而现观智境,同时于智境上现观识境,如是重重悟入缘起,复重重超越缘起,于悟入与超越时,即现证中道。
这里所说的智境与识境,由基来说,可以说为空性与物性;由道来说,可以说为法性与法;由果来说,可以说为如来藏与阿赖耶。
于实际观修中,亦必须将层层智境建立为识境,然后才能加以层层观察,因为凡观察必依心识,必依识觉,当依于识时,便即是将所缘境建立为一重缘起有,复由观察而起智觉,由是始生一重超越识境的智境。必须这样才是实际的观修,而不是但落于名言中求理解的虚妄分别。
若将这样的观修境界说为“空有双运”,亦无不可,但却必须知道,空与有并非居于同一缘起层次,此由上来所说即可知,识境与智境不能同居一个层次。若于弥勒瑜伽行,即是遍计自性相与依他起相不能同一层次。识境与遍计即是兔角喻、智境与依他即是牛角喻。
“除中道外无所有”,所以一切有,都只是“中道有”,这即是胜义的世俗、世俗的胜义。
因此龙树有颂说——
庄严住者具力尊 及宏丽色究竟天
连同心识此三者 可合为一我敢说
具力尊即是身、色究竟天即是界、心识即是智,此三者无有分别,故说“可合为一”。当于究竟离碍时,法身依然要藉身、智、界而成显现。如来的身智界可呈现为报土,亦可呈现为一切情器世界,但这又有甚么分别呢?一切显现无非只是“中道有”,所谓净土与秽土,只是我们背离中道的虚妄分别,这就是龙树所说的“未熟唯依于识觉”。
所以龙树热切地赞颂法界说——
究竟周遍一切边 噫彼莲花亿万千
朵朵含藏鲜花药 办办光明宝庄严
一切情器世界都是莲花世界,因为它是法界的周遍自显现,即是法身自显现。是故结颂言——
有情性实离诸色 由受局限而成界
此即胜义菩提心 法身远离一切碍
于见法身清净时 此即转依智慧海
能满一切有情愿 无价宝珠深海内
于智慧海中依然有能利益有情的宝珠,这便可譬喻为龙树中道。
龙树中道,其实于五地始能悟入。所以在说十地与法身的诸偈颂中,龙树如是说第五难胜地——
通达智与世间明 非唯一趣住禅境
难净世染亦消除 是故名为难胜地
这地位上菩萨的修习,是于禅定中不遣世智(识觉),而且于行持中亦须通达声明、因明、工巧明、医方明等,这亦包括咒术、方术种种,在古代,甚至包括炼金术的研究。何以在禅观以外还须要通达这些世间事务呢?这就即是将一切“外明”都视为佛智藉识而显现、法身藉烦恼而显现,倘若因其为“外”即不去加以了解,那就是只持于智、只持于智境、只持于法身与法界,由是即离中道,而且其所证智寻且又退转为识。
《大般涅槃经》说——
我者,即是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义。[注17]
其实便亦即是这个意思。在这里的“我”,是指法身,如来藏是法身的智境,而“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则正是藉识境而显现的智境。
所以这个“我”,并不是为了迁就外道而说,既说,亦从来未有将之与世间的因缘法混同,在因缘的层次上说之为“真常”。
这个“我”,可说为“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此即说智境不离识境而成显现,识境显现亦从未离开过智境,而智境则并未因此而有任何变异。
因此,《大般涅槃经》说——
所有种种异论、咒术、言语、文字,皆是佛说,非外道说。
有人认为这是“过去佛所说”,不过流传久了,走了样,才成为外道说。这样的理解,未免太过不了解如来藏,难怪就会说如来藏是建立为众生的清净因。
因为法身唯藉烦恼而成显现,所以异论、咒术等等显现,便都即是佛的法身现为烦恼相,《大涅槃经》正是由此层面而说,其意趣等同《维摩经》所言——
于是维摩诘问文殊师利:何等为如来种?
文殊师利言:有身为种、无明有爱为种、贪恚痴为种、四颠倒为种、五盖为种、六入为种、七识处为种、九恼处为种、十不善道为种。以要言之,六十二[外道]见及一切烦恼皆是佛种。[注18]
一切烦恼都是佛种(如来种),自然即是:一切烦恼都是如来藏、都是法身。是故种种异论、咒术、言语、文字等烦恼相,“皆是佛说”,因为这一切都是佛智藉烦恼而成自显现。
那么,有情如何能透过烦恼缠来见本初清净法身呢?
《法界赞》有颂云——
由思于我及我所 由思名言及其基
即由大种和合等 施设四种戏论义
此即是说,行者须知于烦恼缠有四种戏论,那就是:我、我所、名言、名言基。
“我”,由大种和合而成,那即是业因缘起,由观察此缘起,便可去除“我”这戏论。
接着,龙树以兔角喻来说“我所”。我所如兔角,本无所有,由妄想而成为有,这即是识境,因此可以用相依缘起来去除识觉戏论。说相依,即是说识觉依心识而妄想建立。
然后是牛角喻,这则是针对“名言”。牛角不是由妄想而成,但却由名言而成显现,因此,可以悟入相对缘起而证其无自性,这里的相对,是名言与真实的相对,亦即戏论与真如相对。由观察极微无自性,是故决定由极微而成的牛角亦无自性,这观察实在可以通于一切名言法,亦即是观察名言与真实,因为“极微”其实亦是名言。
最后一种戏论,是名言所依基,它包括的范围很广,可以说蕴、处、界皆为其所依,《法界赞》因此便分别说色、声、香、味、触、法等外六入,眼、耳、鼻、舌、身、意等内六入,以及其六识等,即遍十八界而说。于此不拟详说,读者可以自行参阅原颂。
龙树于说此时,着重说明一点:不能说“以识为因”生起外六入。譬如说以鼻识为因然后生起“香”,那么,法界便变成是“香界”。因此,“以识为因”便即是戏论。

在这里,可以说,后起的唯识实在与龙树的观点不同,一切外境唯识变现,那即是以识为因。不同的缘故,是由于龙树着重于般若波罗蜜多的体性,弥勒瑜伽行则着重般若波罗蜜多的行相。着重体性,是故可以凡行相都置之于缘起上,现证其无自性;着重行相,便须将识境加以内外观察,这时候,识就自然成为识境的因。
比较起来,龙树的观行可以说为顿,而弥勒的观行则可说为渐。所以二者的差别,亦可说为顿渐的不同。不过却亦须知,龙树的顿,只利于悟入,而弥勒的渐,却利于现证。瑜伽行中观将心识建立为坛城,坛城则摄集一切法界功德,那虽依然是以识为因,但这心识于观修时则实已等于法身(例如修“迎智尊”),这就即是依龙树的中道(智境与识境双运)来观修瑜伽行。
瑜伽行中观于正式观修前,须先依“九种住心”来作“三等持”。这三等持,目的即在于令行者能将心识等同于法身,也即是说,此时的心识已经是不离烦恼缠的如来藏,这即是心识的实际状况。因此,如来藏绝对不是一切有情可以成佛的唯一清净因,它实在是实际观修的显现基。
这样的建立,既符合龙树的中道,亦符合弥勒的瑜伽行,是故才称为瑜伽行中观。如今有些学人,认为瑜伽行中观即是密宗,密宗偏向于神秘,所以有外道的倾向,那是根本误解了坛城建立的意趣。有人甚至轻率地说,瑜伽行中观理论基础薄弱,不堪一击,由是印度佛教才会受外道摧灭。这些学者不知到底有没有读过密续。随口诽拨,即是对读者不负责任。
龙树所说的这四重戏论,实都由相碍缘起加以遣除,以名言显现基即是心识,以心识为因即是戏论,这戏论实可看成是烦恼缠对如来藏的相碍,行者只须认识相碍,戏论即可遣除。这便即是透过烦恼缠来看如来藏,亦即初地菩萨的现证。颂云——
佛以十力助未熟 加持力似月离碍
然彼若受烦恼缠 是即不能见如来
此中所说的“如来”,应该即是如来藏、法身。
注释
15 下来引颂依拙译,详见本章附录。
16 《楞伽》亦有言(依拙译):
“世尊告言:大慧,有一类外道,溺于无有,依彼见地,断言一切法自性随因坏而无有,即以此分别见而谓兔角无有,彼等乃说一切法无有如兔角。复次,大慧,又有一类外道,见大种、求那、极微,实境 (dravya)、形与位等诸法差别有,故执着于兔无有角而牛有角。
是故大慧,彼等堕入二见而不能了达唯心,彼等欲分别自心[所成]之外境。大慧,身及资具,与所住处,实唯分别而成为有。……
尔时世尊复说与大慧言:菩萨摩诃萨,大慧,须离兔角与牛角、色与空等分别想。如是,大慧,汝与诸菩萨当思维自心所现分别之自性,则当入诸菩萨地,宣说彼等于自心显现中之观修法。”
西方学者Chr.Lindtner,于Nagarjuniana:Studies in the Writings and Philosophy of Nagarjuna一书中,提出龙树造诸论着时,应已熟知当时尚为口传的《楞伽》经义,即于《中论》,亦引用《楞伽》偈颂五次。此《法界赞》所说“兔角”、“牛角”喻,应亦出自《楞伽》。
17 大正·十二,no.374,页407b。
18 大正·十四,no.475,页54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