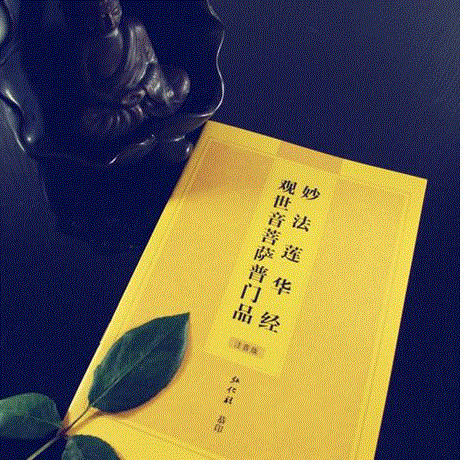方广锠:敦煌《坛经》新出残片跋
发布时间:2022-08-17 12:36:48作者:普门品全文网敦煌《坛经》新出残片跋
方广锠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坛经》是禅宗的基本经典,是中国人所撰且获得“经”之权威的唯一佛典。这一情况,足以奠定《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然而,正因为如此,《坛经》便屡遭厄运。《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载,慧能弟子南阳国师慧忠曾感慨地说:“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它《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後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慧忠逝世於唐代宗大历十年(775年),距离慧能去世的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才60馀年。明乎此,後代《坛经》之出现多种不同的传本,便毫不足怪了。
敦煌本《坛经》的出现引起人们极其浓厚的兴趣,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年代最早的抄本。人们希望通过对敦煌本《坛经》的研究窥见慧能《坛经》的原貌,从而进一步推动对禅宗的研究。因此,本世纪来,依据敦煌本《坛经》进行的新的录校与研究不断涌现,并带动了传世本《坛经》及禅宗的深入研究。
敦煌遗书散藏世界各地,敦煌本《坛经》也有好几个写本。从现有资料看,最早被发现的敦煌本《坛经》是大谷探险队成员吉川小一郎在敦煌得到的ろ36号,册子装。该写本後归旅顺博物馆收藏,在《大谷光瑞氏寄托经卷目录》(稿本,年代不详,约1914年至1916年)、叶恭绰《旅顺关东厅博物馆所存敦煌出土之佛教经典》(载《图书馆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26年)、《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载《新西域记》下卷,1937年)中均有着录。遗憾的是该写本现下落不明。但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有该写本首尾两叶的照片。首叶照片为《坛经》之首,虽然只保存了首题及5行经文,但蕴藏着重要的研究信息;末叶照片为《大辩邪正经》之尾,有题记“显德五年己未岁三月十五……”及杂抄经文。1989年,井之口泰淳、臼田淳三、中田笃郎等在《旧关东厅博物馆所藏大谷探险队将来文书目录》中公布了这两张照片。由于只有这么两张照片,我们现在无法据以判断该写本所抄之《坛经》是否完具。1994年我曾就此事询问过龙谷大学的有关先生,据说当时没有全部拍摄,只拍摄了这么首尾两拍。或者由于原件下落不明的缘故,该号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94年潘重规先生的《敦煌坛经新书》首次利用它作校本。
其次被发现的是藏於英国的S.5475号,也是册子装,首尾完整。1923年由日本矢吹庆辉发现。1928年,《大正藏》第四十八卷公布了它的录文;1930年,《鸣沙馀韵》公布了它的照片;五十年代,大英博物馆发行了缩微胶卷。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敦煌本《坛经》的研究大抵依据这个抄本。
第三个被发现的是藏於北图的冈48号。该号卷轴装,只抄写了《坛经》的后部分,有尾题。1930年陈垣先生曾用附注的形式在《敦煌劫馀录》中作了着录,但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五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初,北图两度公开该号的缩微胶卷,仍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1986年黄永武先生《敦煌最新目录》再次着录。1991年日本田中良昭先生首次发表录校、研究。
第四个被发现的是现在藏於敦煌县博物馆的敦博077号。册子装,首尾完整。该号原藏敦煌任子宜家,据任称乃1935年得自敦煌千佛山上寺。该写本抄写禅文献多件,《坛经》是其中之一。另还有孤独沛《南宗定是非论》、神会《坛语》、净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四十年代向达先生赴敦煌考察时曾对上述文献二度过录,并在所撰《西征小记》(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中作了着录,世人由此知道该写本的存在。向达先生的这两个过录本,一个后来赠送给吕澂先生,吕澂先生曾经将其中的净觉撰《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整理发表在《现代佛学》1961年第四期上,其馀文献则未整理发表。该过录本现由周绍良先生收藏。另一个过录本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但此後原写本一直下落不明,很多有心人四处寻访。1983年周绍良先生发现它被敦煌县博物馆收藏,便组织拍摄照片。1993年,杨曾文先生首次发表录校研究。任继愈先生主编《佛教宗派全书·禅宗编》(江苏古籍出版社)收有该号的照片。这是现知敦煌本《坛经》中抄写质量最高,校勘、研究价值最大者。
上面就是至今为止学术界知道的敦煌本《坛经》的四个写本的简单情况。
1997年4月,笔者在整理北图藏敦煌遗书时,从尚未定名的遗书中鉴定出一件《坛经》残片,现公布於下,这是我们现知的第五号敦煌《坛经》写本。
该遗书编号为北敦8958号,仅一纸,首被剪断尾脱,17厘米×25.3厘米,有乌丝栏,共10行。但仅前5行抄有经文,後5行空白。行17字。所抄内容如下:
(前剪)
1、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愿力。今既发四弘誓
2、愿讫,与善知识无相忏悔三世罪障。大师言:善

3、知识!归依觉,两足尊;归依正,离欲尊;归依净,
4、众中尊。从今已後,称佛为师,更不归依馀邪迷
5、外道。愿自三宝
(後缺)
原卷为卷轴装。上述5行文字自首行“迷妄”至“大师言:善知识”,及“大师言:善知识”至末行“三宝”分属《坛经》的先後两段经文,中间缺漏140馀字。显然,这是涉“大师言:善知识”重文而漏抄的一例。古代敦煌抄经,因原卷错抄而作废时,为节约纸张,往往将错抄部分剪下,接粘空纸後继续抄写。而剪下之错抄部分则备作他用。本号背面抄有其它文献,就是证明。这种例子,在敦煌遗书中颇多见。本号背面所抄为“午时无常偈”、“中夜无常偈”、“后[夜]无常偈”等6行。亦未抄完便放弃,应属于杂抄之类。
应该说明的是,该残片原编号为“有79号”,属于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四大部分之《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部分。关于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四大部分形成及《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部分的情况,请参见拙作《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勘察初记》(载《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二期)。这部分敦煌遗书共计1192号,其中有229号尚未定名,有79号就属于没有定名的部分。在我们新编的《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中,北图所藏敦煌遗书将全部统一重新编号,该号将被正式定为北敦8958号。
北敦8958号被发现后,即公诸同好。已经有先生据此进行研究,故在此不拟对它的校勘价值再作评述。我想谈的是另外一些问题。
上述五种敦煌本《坛经》,三种为册子本,二种为卷轴本。在北敦8958号被发现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卷轴本只有北冈48号一件。而从北冈48号形态看,显然不是一个正规的写经,而属于经文杂抄。所以,我以前一直有一个推想,以为禅宗南宗,起码是南宗神会系既以《坛经》作为传法的依凭,门弟子人手一部,随身携带,则《坛经》的标准形态可能就是册子本。如果这种推想可以成立,则册子本这种装帧形式的产生年代将大大提前。不过,由于这种推想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所以始终不敢提出,只是在自己心中琢磨。但从此次发现的北敦8958号的形态看,它的纸张是常见的写经纸。长度虽已不可测,但高度与同时代写经相符。有乌丝栏,规格也与同时代写经相符。行17字。北敦8958号虽是废弃的错稿,唯其如此,说明当初抄写时是很认真的,抄成的正稿质量一定上乘。凡此种种,都说明敦煌曾经存在过以标准的卷轴本形态抄写的《坛经》。所以,我以前的那种推想不能成立。
现存敦煌本《坛经》均属南宗神会系传本,这一点大概无可怀疑。神会系以《坛经》作为传法的依凭,而北敦8958号的形态反映敦煌当地亦抄写《坛经》。由此,南宗神会系之传到敦煌,应该说是确凿无疑的。敦煌本《坛经》既有卷轴本,又有册子本,两种流传形态反映了时代的差异,亦即反映了南宗神会系曾经在敦煌长期流传,绵绵不绝。
北宋时,敦煌孤悬西北,同时向北宋王朝与辽王朝称臣朝贡,似乎实行等距离外交。但辽王朝盛行《华严》,禁绝《坛经》。敦煌却流行禅宗与《坛经》,采用北宋王朝的纪年。由此看来,表面上的等距离外交不能掩盖敦煌的亲宋疏辽的实质。
北敦8958号证明敦煌至少抄写过一号质量较好的卷轴本《坛经》。但在现存敦煌遗书中却没有发现。由于敦煌遗书绝大多数已经面世,所以恐怕这一件《坛经》根本就没有入藏藏经洞,自然也不可能被发现。站在敦煌遗书“废弃说”的立场上来看,这是很正常的。站在“避难说”或“图书馆说”的立场上来看,这种情况则是奇怪的,或难以理解的。所以,敦煌遗书中存在着错抄的北敦8958号,却没有北敦8958号所从剪下的那卷抄写正确的《坛经》,正是敦煌遗书“废弃说”的又一个证明。
至今为止,从事敦煌本《坛经》整理的先生往往参考其它系统的《坛经》流通本,来修订、改正敦煌本。在敦煌《坛经》诸本没有充分被发掘之前,那种方式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敦煌本《坛经》已经大量被发现的今天,我以为排除所有其它系统《坛经》的干扰,纯粹采用敦煌本互校,作成一个敦煌本《坛经》的精校本,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或出发点,可能更有意义。
最后还应该提及西夏译《坛经》残片。
此类残片最早发现於本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罗福成曾发表研究论文,日本学者也曾经发表过研究成果。其後又续有发现,现分藏各处,计12个残页。有史金波先生考释译文《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三期)。据史金波先生告诉笔者,从纸张、笔迹等形态看,他考察过的诸残页原来均属同一写本。西夏文《坛经》是根据汉文《坛经》翻译的,有的研究者认为,它的底本就是敦煌本。无论如何,在现存诸《坛经》传本中,西夏文本的年代与流行地域最接近敦煌本,行文也最接近敦煌本,因此它可以成为我们研究敦煌本《坛经》时的重要参考资料。